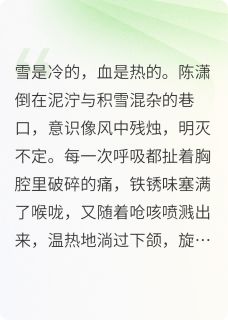悬疑小说《雪夜救我的神医是买凶杀我的主谋》,是小小小汐最新写的一本现代言情类小说。主角陈潇方小小卷入了一个离奇的谜案中,故事紧张刺激,引人入胜。读者将跟随主角一起解开谜团。在那极隐蔽的、右腕内侧极不起眼的地方,靠近脉搏的位置——确确实实,纹着一朵小小的、嫣红的、五瓣梅花。……唢呐还在吹,一声……
章节预览
雪是冷的,血是热的。陈潇倒在泥泞与积雪混杂的巷口,意识像风中残烛,明灭不定。
每一次呼吸都扯着胸腔里破碎的痛,铁锈味塞满了喉咙,又随着呛咳喷溅出来,
温热地淌过下颌,旋即被无情的寒意冻结。视野模糊地晃动着,
巷子外街市的灯火晕开成一团团混沌的光斑,喧嚣隔了一层厚厚的膜,遥远得不似人间。
只有濒死的寒冷和剧痛真实无比。三刀。一刀在腹,两刀在背。出手的是他视若手足的兄弟,
酒里下了药,笑容还挂在脸上,匕首的冷光就已经没入了他的身体。
那声“为什么”哽在喉头,问不出,也不必再问。推金倒玉般的信任,
原来真是这世上最可笑的一厢情愿。他听着自己的血漫出身体,汩汕地流进血水里,
那声音细微又惊心。力气正一点点被抽空,连抬起手指的意念都无法驱动肢体。
要死在这里了。像条野狗,死在一个无人知晓的雪夜。也好。他闭上眼,
几乎要放任自己沉入那片永恒的黑暗。就在这时,细微的脚步声踏雪而来,很轻,很稳,
停在了他眼前。竭力掀开沉重的眼皮,朦胧的视线里,最先闯入的是一双鞋。素白的缎面,
边缘绣着细细的枝桠,点缀着几朵嫣红的梅花,洁净得与这污秽血腥的雪地格格不入。
顺着那素履往上,是月白的裙裾,再往上…他努力对焦,对上一双眼睛。清澈,乌黑,
像浸在冰水里的墨玉,倒映着他奄奄一息的狼狈模样,却没有丝毫惊惧,
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平静。雪光映照着她纤细的身影,她蹲下身,
一股极淡的、清苦的药香驱散了些许浓重的血腥气。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一只微凉的手轻轻探了探他颈侧的脉息,动作熟练而轻柔。“别怕,”她的声音也像这雪夜,
清冷冷的,却奇异地抚平了他意识边缘最后那点惊惶,“能救。”这是他彻底失去意识前,
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再醒来时,先嗅到的是那股熟悉的清苦药香,萦绕在鼻尖。
他躺在一张干净的床榻上,身上盖着半旧的棉被,伤口处传来被妥善包扎后的闷痛。
阳光透过糊着浅色窗纸的格子窗,在地面投下温暖的光斑。一时间,他有些恍惚,
不知今夕何夕。轻微的响动传来,他侧过头,看见那道纤细的身影正背对着他,
在窗边的木桌前捣药。乌黑的发丝用一根简单的木簪绾起,露出细白的一截脖颈。
阳光勾勒着她认真的侧影,手腕起落间,是轻柔却有力的节奏。似乎察觉到他的注视,
她转过身来。四目相对。她的眼睛依旧清澈得能一眼望到底,只是此刻在光线下,
能看清那眼睫长而密,像两把小扇子。“你醒了?”她放下药杵走过来,声音平稳,
听不出太多情绪,“昏睡了三天,发热反复,总算熬过来了。”“姑…娘……”他开口,
声音干涩得吓人。她扶他稍稍起身,递过一碗温水,小心地喂他喝下。水温正好,
润泽了他干裂的嘴唇和灼痛的喉咙。“我叫方小小,”她放下碗,重新检查他腹部的绷带,
“是回春堂的学徒。你伤得很重,但没伤到根本,好生将养些时日,能恢复。”“陈…潇。
”他哑声道,“多谢…姑娘救命之恩。”方小小摇摇头,
示意不必言谢:“那晚去给师傅送东西,回来碰巧了。”她说话简洁,没有多余的好奇,
比如他为何身受重伤,仇家是谁。接下来的日子,是陈潇生命中一段近乎凝滞的时光。
伤口在方小小一日三次的换药和汤剂下,缓慢却持续地愈合。她话不多,
大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做着手头的事——煎药、捣药、替他清理伤口、准备清淡的饭食。
这间小小的、陈设简单的屋子,仿佛与世隔绝,只有弥漫不散的药香和窗外日升月落的光影。
陈潇常常靠着枕头,看她忙碌。看她如何细致地将草药分门别类,
看她如何专注地控制火候煎药,看她因为捣药久了微微泛红的手掌心。
她就像一株安静生长在幽谷里的植物,有一种恒定、包容的力量。偶尔,
他会在夜里被噩梦惊醒,刀光、背叛、刺骨的寒冷和痛楚交替上演。冷汗涔涔时,
只要闻到空气中那缕淡淡的药香,听到外间她或许翻身的细微动静,
那狂跳的心便能慢慢沉静下来。他开始对她说话。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见闻,
甚至带着笨拙的笑话。她大多只是听着,偶尔嘴角会极轻地弯一下,那一点微小的弧度,
就能让他莫名高兴许久。他从未提及那夜的暗算,那个名字是心底一块溃烂的疮疤,
一碰就痛彻心扉。她也从不问。有一天午后,阳光特别好,她扶他到窗边坐着晒一会儿太阳。
她坐在一旁低头缝补一件旧衣,针脚细密匀称。他忽然问:“小小,你救我的时候,
不怕惹上麻烦吗?”方小小抬起头,目光落在他脸上,很平静:“怕。但你是伤者。
”就那么简单的几个字。陈潇却觉得胸腔里被什么东西塞满了,又酸又胀。他在这双眼睛里,
看不到任何算计、任何虚伪,只有一种近乎纯粹的直白。他曾经坚信不疑的情谊轰然倒塌,
而这个素昧平生的女子,却给了他一片从未奢望过的净土。信任这东西,一旦碎了,
本以为再难拼凑。可原来,遇上对的人,它自己会悄悄滋生。他能下地的那天,
扶着墙慢慢走到院子里。方小小正在晾晒药材,回头看见他,愣了一下,
随即快步过来扶住他的胳膊。“刚好些,别逞强。”他借着她的力站稳,
深吸了一口冬日清冽的空气,胸腔里虽还带着隐痛,却有种新生的畅快。“小小,
”他侧头看她,阳光落在她细软的绒毛上,像是镀了一层柔光,“我好像…重活了一次。
”方小小的睫毛颤了颤,没说话。日子一天天过去,陈潇的伤好了七七八八,
甚至能在院子里帮她劈一些柴火。他不再是需要全副身心照顾的伤患,他们之间,
似乎有什么东西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会在她尝药汤烫不烫时,下意识地屏住呼吸。
她会在他笨拙地想帮忙却打翻筛子时,忍不住轻笑出声。眼神交汇的次数越来越多,
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空气里弥漫着无声的、细微的悸动。除夕夜,
小小的屋子里生了炭盆,比平日暖和许多。窗外不时传来鞭炮的噼啪声和隐约的笑语。
方小小备了几样简单的小菜,还有一壶温过的酒。“你伤未全好,只许喝一点。
”她给他斟了浅浅一杯茶。酒液温热,滑入喉中,带起一股暖流。
陈潇看着她被炭火烤得微红的脸颊,心跳得有些快。“小小,”他放下酒杯,
声音在安静的屋里显得格外清晰,“等我能走了,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
”方小小握着筷子的手顿了顿,抬起头看他。“我没什么大本事,但还有些力气,
总能找到营生。我……”他深吸一口气,像是要鼓起所有的勇气,“我不想再一个人了。
我想…和你一起。”屋子里只有炭火偶尔爆开的轻微哔哔声。方小小的眼睛映着跳动的火光,
看不清情绪。良久,她轻轻开口:“陈潇,你并不真的了解我。”“我了解!
”他急切地倾过身,握住她放在桌上的手。她的指尖微凉,他一把握住,像是要捂热她,
也像是要抓住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我知道你心善,知道你医术好,知道你安静却坚韧,
知道你一个人撑得很辛苦……我知道这些就够了!小小,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
它早就是你的了。”他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郑重得像起誓:“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但我知道,从今往后,陈潇余生,只为小小而活。”方小小的手指在他掌心微微颤了一下,
想要抽回,却最终停住。她的眼睫低垂下去,遮住了所有可能流露的情绪。
就在陈潇的心一点点沉下去时,她极轻极轻地,回握了一下他的手。虽轻微,
却足以让陈潇狂喜。他忍不住笑起来,眼底却有些发酸。他抬起她的手,小心翼翼地,
珍而重之地,在她微凉的指尖印下一个轻如羽毛的吻。承诺既出,山海无移。伤愈后,
陈潇并未立刻离开。他在回春堂附近找了个短工,踏实肯干,赚的钱不多,
却总会记得给方小小带一支新开的梅花,或者一块铺子里新出的甜糕。他看着她的时候,
眼睛里有光。那种经历过绝望后,重新燃起的、炽热而专注的光。
方小小似乎还是那个安静的女子,但眼角眉梢,终究是染上了几分柔软的春意。
她会默默把他带回来的梅花**清水瓶里,会把他买的糕点多分他一半。
婚期定在春暖花开的三月。陈潇租下了一个小院子,不大,但干净齐整。他亲手糊了窗纸,
修了篱笆,在院子里种下一株小小的梅树苗。“等明年冬天,我们就能在自家院子里赏梅了。
”他拉着她的手,兴奋地规划着未来,“到时候,我再盘个小铺面,
你不用那么辛苦采药看诊,喜欢就做,不喜欢就在家歇着……”方小小听着,只是笑,
笑容很浅,却直达眼底。大婚当日,天未亮陈潇就起身了。穿上崭新的红袍,
胸口系着大红花,他看着镜中眉眼带笑的自己,
几乎要认不出这就是那个雪夜里奄奄一息的绝望之人。锣鼓声,鞭炮声,
喧闹的人声由远及近。花轿临门了。陈潇的心跳得像擂鼓,手心全是汗。
他在一众街坊邻居善意的哄笑声中,快步走向那顶披红挂彩的轿子。他的小小,就在里面。
从今天起,就是他名正言顺的妻。他正要上前迎新娘,街角突然跑来一个半大的孩子,
手里举着一封信,嚷嚷着:“哪位是陈潇陈公子?有人让我把这信给你,
说是故人送的新婚贺礼!”陈潇一愣,心下有些诧异。他在此地并无故旧。但大喜的日子,
或许是以前的朋友辗转得知了消息?他笑着接过信,拍了拍小孩的头,塞了几个铜钱,
顺手便将信拆开。唢呐声还在欢快地吹打着,周遭是喧腾的热闹。红色的信笺,
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信纸。上面的字迹却凌厉如刀锋,瞬间劈开所有喜庆的泡沫,
将他眼底的笑意冻结成冰——“雪夜三刀,穿腹透背,可还痛否?遥祝新婚之喜。
另:当日主谋,右腕内侧,纹有一朵小小梅花。”每一个字都像一把烧红的匕首,
狠狠捅进他的眼眶,直刺脑髓!唢呐声、鞭炮声、欢笑声……刹那间全部褪得干干净净,
世界死寂一片。只有那几行字在眼前无限放大,扭曲,狰狞如鬼魅。
右腕内侧…小小梅花……他猛地抬头,
血红的眼睛死死盯住那只正从花轿中伸出的、戴着龙凤呈祥喜帕的新娘的手。白皙的腕子上,
空空如也。不……不是那里。他记得,有一次她捣药时,袖口滑落,他瞥见过。
在那极隐蔽的、右腕内侧极不起眼的地方,靠近脉搏的位置——确确实实,
纹着一朵小小的、嫣红的、五瓣梅花。……唢呐还在吹,一声声,刺耳得像是送葬的哀乐。
花轿的红绸还在眼前晃动,像泼开的血,刺得他眼眶生疼。那封信笺飘落在脚边,无人理会。
天的锣鼓、鞭炮的碎屑、街坊哄笑的声浪——所有的一切都隔了一层厚厚的、嗡嗡作响的膜,
变得模糊不清,扭曲变形。世界在他脚下裂开一道深渊,寒气从地底喷涌而出,
瞬间将他冻僵。右腕内侧。小小梅花。八个字,比那夜捅进身体的三把刀子更锋利,更恶毒,
精准地剜碎了他刚刚拼凑起来的心。那只戴着喜帕的手还伸在轿门外,指尖微微蜷着,白皙,
纤细,他曾无数次握在掌心,珍视地吻过。此刻却像淬了毒的钩爪,要挖出他的五脏六腑。
他记得。他怎么会不记得?那次她捣药久了,袖口滑落,他无意间瞥见。在那极隐秘的腕内,
脉搏跳动的地方,有一朵小小的、嫣红的五瓣梅花。当时他还笑,说你这学医的姑娘,
怎么还学人纹这风月东西。她当时怎么回的?她只是极快地拉下袖子,遮住了,淡淡说一句,
小时候贪玩,胡乱刺的。胡乱刺的……每一个甜美的过往,此刻都成了扎向自己的刀。
她清澈的眼眸,悲悯的神情,那句“别怕,能救”,她喂到他唇边的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