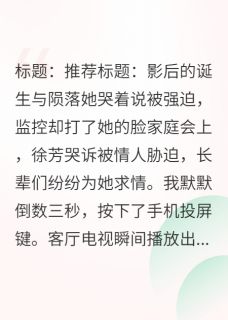这本《她哭着说被强迫,监控却打她的脸》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李威徐芳的故事非常好看,书荒的小伙伴们看过来!小说精彩节选他死死盯着我的手机屏幕,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里,被一种更深沉、更狂暴的东西取代——那是被最信任的人联手捅刀、图谋家产的震……
章节预览
家庭会上,徐芳哭诉被情人胁迫,长辈们纷纷为她求情。我默默倒数三秒,
按下了手机投屏键。客厅电视瞬间播放出监控画面:她穿着我送的吊带裙,
笑着挽住男人脖子献上热吻。“强迫?”我晃了晃离婚协议,“签了吧,净身出户。
”她瘫软在地时,我手机响了——是她情人发来的消息:“芳,你老公那笔贷款批下来了,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正文指尖在口袋里那个冰冷的金属方块上轻轻一点,
动作流畅得如同呼吸。下一秒,客厅那面巨大的、平时用来追剧看电影的液晶电视屏幕,
“嗡”地一声亮了起来,瞬间驱散了房间里弥漫的压抑悲情。刺眼的光芒让所有人,
包括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徐芳,都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或抬手遮挡。屏幕上出现的,
不是什么电影片段,也不是什么温馨的家庭照片。
正是我家门口那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对准公共楼道的监控摄像头视角。
画质清晰得纤毫毕现,连楼道墙壁上剥落的一小块墙皮都看得清清楚楚。画面无声,
却比任何控诉都更有力量。日期时间水印,清晰地显示着:2023年7月15日,
晚上9点37分。正是徐芳口口声声被那个男人“暴力胁迫”、“强行拖走”的那一天晚上。
画面里,我家的防盗门打开了。
穿着那件我上周才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的、价值不菲的墨绿色真丝吊带裙的徐芳,
脚步轻盈地走了出来。她脸上非但没有一丝一毫被“胁迫”的恐惧或痛苦,
反而洋溢着一种近乎沉醉的、明媚的笑容,像是吸饱了阳光的花朵。她甚至没有立刻关门,
而是转过身,对着门内的人——那个此刻还隐在门后阴影里的男人——娇俏地伸出手指,
点了点自己饱满的嘴唇,做了个飞吻的动作。动作流畅自然,带着一种熟稔的亲昵。紧接着,
那个男人也走了出来。正是徐芳口中那个“胁迫”她的恶魔——李威。一个我认识的人,
一个曾经在酒桌上和我称兄道弟、拍着胸脯说有事他罩着的“朋友”。
李威脸上带着同样餍足而轻松的笑容,伸手自然地揽住了徐芳纤细的腰肢。
徐芳非但没有抗拒,反而顺势依偎过去,侧过头,主动地、毫不犹豫地吻上了李威的侧脸。
那是一个响亮的、带着明显占有欲和满足感的吻。李威显然很受用,他低下头,
两人旁若无人地在楼道里拥吻起来。徐芳的手臂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李威的脖子,
身体紧紧贴着他,那份投入和热情,是我在她身上许久未曾见过的。足足过了十几秒,
两人才意犹未尽地分开。徐芳整理了一下被弄乱的裙摆,脸上依旧是那抹娇艳的笑容,
她甚至踮起脚尖,凑在李威耳边说了句什么。李威听完,哈哈大笑起来,
伸手宠溺地捏了捏她的脸颊,然后才转身,哼着不成调的小曲,脚步轻快地走向电梯间。
徐芳则一直倚在门框边,痴痴地望着他离开的方向,脸上的笑容灿烂得晃眼,
直到电梯门完全合拢下行,她才带着一种心满意足的神情,慢慢关上了家门。整个视频不长,
一分多钟。但这一分多钟,如同一个无形的、巨大的耳光,带着雷霆万钧之力,
狠狠地、精准地抽在了客厅中央、那个前一秒还在哭诉“被强迫”的女人脸上。时间,
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按下了暂停键。客厅里陷入了一种死寂。绝对的、真空般的死寂。
连空气都停止了流动,只剩下电视机屏幕发出的、冰冷而稳定的光芒,映照着每一张脸。
我母亲拿着纸巾的手僵在半空,纸巾无声地飘落在地毯上。她张着嘴,眼睛瞪得极大,
难以置信地看着屏幕,又看看徐芳,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个朝夕相处的儿媳。
她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只剩下一种被巨大欺骗击中后的惨白和茫然。
我父亲紧锁的眉头骤然松开,随即又拧得更紧,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
他那双历经风霜、看透世事的眼睛里,此刻翻涌着滔天的怒火和被愚弄的耻辱,
死死地盯着徐芳,胸膛剧烈起伏着,粗重的喘息声在寂静中异常清晰。他放在膝盖上的手,
已经紧握成拳,指节捏得发白,微微颤抖。刚才还在为徐芳“仗义执言”的姨妈和表姑,
此刻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所有未出口的劝解和同情都噎在喉咙里,
化作满脸的惊愕和尴尬。她们的目光在冰冷的屏幕和面无人色的徐芳之间快速切换,
眼神里充满了震惊、鄙夷,还有一种被当众戏耍的恼怒,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而风暴的中心,徐芳。她脸上那精心扮演的、梨花带雨的悲戚表情,
如同被投入烈火中的劣质面具,在监控画面亮起的第一秒就彻底碎裂、崩塌、灰飞烟灭。
所有的泪水、所有的控诉、所有的柔弱无助,都在那清晰的画面面前,
被瞬间蒸发得干干净净。她的身体猛地一僵,像被高压电流击中。
那双前一秒还盛满泪水、楚楚可怜的眼睛,此刻瞪得几乎要裂开,
瞳孔在屏幕强光的**下急剧收缩,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纯粹的惊恐。
仿佛看到了地狱的入口在她脚下豁然洞开。惨白。那是一种足以让吸血鬼都自惭形秽的惨白,
迅速地从她的脸颊蔓延至脖颈,再扩散到全身。她精心涂抹的腮红和粉底,
此刻成了最拙劣的讽刺,衬得她整张脸如同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女鬼。
“不…不可能…”一声破碎的、气若游丝的**从她失血的嘴唇间挤出来,微弱得如同蚊蚋。
这声音像是打开了她身体某个崩溃的开关。她像是被抽掉了全身的骨头,
又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巨力狠狠击中。身体剧烈地晃了一下,然后,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木偶,
从那张她引以为傲的米白色沙发上,软绵绵地、毫无生气地滑落下来,
“噗通”一声重重地瘫倒在冰冷光滑的瓷砖地板上。那身昂贵的真丝吊带裙,
此刻皱巴巴地裹在她瘫软的身体上,像一块肮脏的抹布。她瘫在那里,像一滩融化的蜡,
头无力地垂着,散乱的头发遮住了她大半张脸,
只有身体还在无法控制地、筛糠般剧烈颤抖着。刚才还响彻客厅的、悲愤的哭泣声,
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喉咙深处发出的、濒死般的、断断续续的“嗬…嗬…”声。
谎言,在铁铸般的证据面前,被碾得粉碎。连一丝辩驳的余地都没有留下。
客厅里那令人窒息的死寂还在蔓延,像一层冰冷厚重的油污,糊在每个人的口鼻上。
亲戚们惊愕、鄙夷、尴尬的目光如同探照灯,牢牢钉死在地板上那滩融化的“蜡像”上。
父母的呼吸粗重,父亲铁青着脸,母亲捂住了嘴,身体微微发颤,
眼中满是震惊后的巨大失望和被欺骗的痛楚。在这片足以压垮任何人的寂静中,
我缓缓站起身。动作不疾不徐,甚至带着一种事不关己的冷漠。皮鞋踩在地砖上,
发出清晰而规律的“嗒…嗒…”声,每一步都像敲在紧绷的神经末梢上。
我从西装内袋里抽出一个薄薄的牛皮纸文件袋,动作利落地解开缠绕的白色棉线。
几张打印得整整齐齐的A4纸被抽了出来,在空气中发出清脆的“哗啦”声。
我走到徐芳面前。她没有抬头,或者说,她根本没有力气抬头。
浓密的头发像一丛枯萎的水草,杂乱地覆盖着她的脸,
只有肩膀还在无法抑制地、神经质地抽动。“强迫?”我的声音不高,
平静得像是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日常琐事,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
清晰地钻进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我微微俯身,将手中的那叠纸在她眼前晃了晃,
纸张的边缘几乎要擦到她低垂的鼻尖。“签了吧,”我说,语调平稳得没有一丝波澜,
“离婚协议。看清楚条款,尤其是财产分割那部分。你,净身出户。”“净身出户”四个字,
像四颗冰冷的子弹,一字一顿,精准地射入徐芳溃不成军的意识里。她瘫软的身体猛地一颤,
像垂死的鱼被扔上了滚烫的沙滩。一直低垂的头颅终于费力地、极其缓慢地抬了起来。
那张脸,惨白得如同新刷的石灰墙,泪痕、晕开的眼线和睫毛膏混在一起,
在她脸上糊成一片狼藉的、肮脏的油彩。精心描画的眉眼此刻只剩下空洞和茫然,眼神涣散,
找不到焦点,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嘴唇微微张开,颤抖着,却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
只有急促而紊乱的喘息声。她看着那份悬在眼前的离婚协议,仿佛那不是几张纸,
而是一把悬在头顶、即将落下的铡刀。
就在这紧绷的、令人窒息的时刻——“嗡嗡嗡…”一阵突兀的、带着震动感的手机**,
尖锐地撕裂了客厅的死寂。声音来自我的裤袋。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地上徐芳那涣散绝望的眼神,都下意识地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吸引,聚焦到我身上。
我没有丝毫意外,仿佛一直在等待这个信号。掏出手机,屏幕亮着,
显示着一条来自“李威”的新微信消息。我的手指在屏幕上随意地滑动解锁,点开信息。
屏幕的光映亮了我的脸,依旧是那副平静无波的表情。我将手机屏幕翻转过来,
让那行刺眼的文字清晰地暴露在客厅明亮的顶灯下,暴露在每一双惊疑不定的眼睛里。
李威的头像旁边,白底黑字,冷酷而清晰地显示着:【芳,你老公那笔200万的经营贷款,
银行那边刚通知我,批下来了!钱下周一到他账上。你那边怎么样?搞定他爸妈没?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空气,在这一刻彻底凝固了。我父亲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动作之大带倒了旁边的水杯,玻璃碎裂的声音清脆刺耳,水渍在地毯上迅速洇开一大片深色。
他死死盯着我的手机屏幕,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里,
被一种更深沉、更狂暴的东西取代——那是被最信任的人联手捅刀、图谋家产的震怒和杀意!
他额头上的青筋如同盘踞的毒蛇,根根暴起,剧烈地搏动着,
粗重的喘息声如同拉动的破风箱,胸膛剧烈起伏,似乎下一秒就要爆炸开来。
他伸手指着瘫在地上的徐芳,手臂抖得厉害,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只有喉咙里发出“嗬嗬”的、野兽般的低吼。我母亲发出一声短促而凄厉的抽气,
像是被人扼住了喉咙。她用手死死捂住嘴,身体晃了晃,脸色白得吓人,
眼神里充满了极度的惊恐和后怕,仿佛看到了最亲近的人被推下万丈深渊。
她踉跄着后退一步,撞在沙发扶手上才勉强站稳,泪水瞬间决堤,无声地汹涌而出。
亲戚们更是彻底炸开了锅!短暂的死寂后,是压抑不住的、愤怒的惊呼和咒骂。“天哪!
蛇蝎心肠啊!”“这…这简直是要杀人啊!”“合伙骗钱?!还想动手?!太毒了!
”“报警!阿飞!赶紧报警抓这对狗男女!”“徐芳!你还是不是人?!罗家哪里对不起你?
!”指责、唾骂、难以置信的惊呼,如同沸腾的油锅,瞬间将整个客厅淹没。
每一道目光都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徐芳身上。而徐芳,在看清那条信息内容的瞬间,
身体如同被无形的巨锤狠狠砸中。她猛地抬起头,涣散的眼神聚焦了一瞬,
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尖大小,里面充满了极致的恐惧和难以置信的绝望。
那眼神仿佛在说:怎么可能?李威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不!不是的!他胡说!
他陷害我!”一声凄厉得不似人声的尖叫猛地从她喉咙里爆发出来,
带着一种垂死挣扎的疯狂。她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困兽,爆发出最后的力量,
手脚并用地想要从地上爬起来,扑向我的手机,想要毁灭那铁一般的证据。
她的动作是那样绝望而疯狂,带着一种同归于尽的凶狠。然而,
她的身体早已被刚才的打击抽空了所有力气,刚撑起一点,就再次重重地摔回冰冷的地砖上。
膝盖磕在地面发出沉闷的响声,她甚至顾不上疼痛,只是徒劳地伸长手臂,
五指痉挛般抓挠着空气,距离我的裤脚还有半米远,却如同隔着无法逾越的天堑。“罗飞!
是他!是李威那个**!是他逼我这么做的!他…他拿捏着我的把柄!他威胁我!
贷款…贷款的事我真的不知情!是他!都是他!他想害你!他想吞掉你的钱!
”她语无伦次地嘶喊着,涕泪横流,声音嘶哑破裂,试图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李威身上,
试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指着我的手机屏幕,手指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
眼神混乱而癫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在地板上狼狈不堪地挣扎、哭嚎、甩锅,
看着她精心构筑的谎言堡垒在接踵而至的铁证面前彻底坍塌,
连带着她最后一丝伪装也片片剥落,露出底下那自私贪婪、丑陋不堪的内核。她的控诉,
她的辩解,在我耳中,不过是败犬临死前毫无意义的哀鸣。心底那片早已冰封的荒原上,
连最后一丝名为“怜悯”的余烬也彻底熄灭了。只剩下一种极致的冰冷和厌弃。
我没有再给她哪怕一个字的回应,也没有再看她一眼。仿佛地上那团歇斯底里的东西,
只是一堆需要被及时清理的垃圾。我平静地收回手机,
视线转向暴怒的父亲和摇摇欲坠、泪流满面的母亲。他们的痛苦和愤怒是真实的,但此刻,
我需要他们冷静。“爸,妈,”我的声音不高,却异常沉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穿透了客厅里的嘈杂,“这里太吵了。我们换个地方谈。关于这笔‘意外之财’,
还有接下来该怎么处理这对‘合作伙伴’,我有计划。”说完,我直接迈步,
皮鞋踩过冰冷的地砖,没有半分迟疑,
绕开了地上那滩还在试图抓住我裤脚、发出绝望呜咽的“障碍物”。我走到玄关,
拿起挂在衣帽架上的车钥匙。金属的冰冷触感传递到掌心,带来一丝奇异的镇定。“去书房。
”我对父母说,语气是不容反驳的肯定句。随即,
目光扫过客厅里那些惊魂未定、义愤填膺的亲戚,“各位长辈,今天辛苦了,
家丑让大家见笑。改天我再登门致谢。现在,请回吧。”话语礼貌,却带着送客的决绝。
亲戚们面面相觑,看着地上彻底崩溃的徐芳,又看看脸色铁青的老罗和他悲痛欲绝的妻子,
再看看我这个从头到尾冷静得不像当事人的儿子,最终都识趣地、带着复杂的表情,
默默地开始收拾东西离开。没有人再试图为徐芳说一句话,投向她的最后几瞥,
只剩下彻底的鄙夷和唾弃。客厅里很快只剩下徐芳绝望的呜咽、父母沉重的呼吸,
和我手中钥匙碰撞的轻微声响。地狱的画卷在她面前刚刚展开序章,而我的反击,
才真正开始。书房厚重的红木门在身后合拢,发出沉闷的“咔哒”一声,
将客厅里徐芳那断断续续、如同鬼泣般的呜咽和混乱彻底隔绝在外。瞬间,
世界仿佛被抽离了所有噪音,只剩下一种紧绷的、风雨欲来的死寂。
空气里弥漫着上好木料、陈旧书籍和未散尽的雪茄混合的味道,这本该是父亲最放松的空间,
此刻却凝重得如同审判庭。父亲像一头被彻底激怒的雄狮,胸膛剧烈起伏着,
粗重的喘息在寂静中格外刺耳。他几步跨到巨大的红木书桌后面,没有坐下,
而是双手撑在光滑的桌面上,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身体微微前倾,
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住我,里面燃烧着熊熊的怒火和被至亲背叛的刻骨耻辱。“说!
”他的声音如同砂纸摩擦铁器,嘶哑而低沉,带着一种极力压抑的狂暴,
“那笔贷款到底怎么回事?!李威那个畜生!还有徐芳那个毒妇!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动手?!他们还想怎么动手?!是不是想要我们全家的命?!
”最后一个问题几乎是吼出来的,饱含着惊怒交加的后怕。他猛地一掌拍在厚实的桌面上,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震得桌上的笔筒都跳了一下。母亲坐在书桌旁的真皮单人沙发里,
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魂。她脸上泪痕未干,身体还在无法控制地微微颤抖,
一只手紧紧抓着沙发扶手,指节同样捏得发白,另一只手则无意识地揪着衣襟。
她的眼神空洞地望着虚空某一点,充满了劫后余生的恐惧和巨大的茫然失措。
丈夫的暴怒似乎让她更加惊惶,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声音,只有眼泪无声地再次滑落。
我走到书桌对面的另一张沙发前,没有立刻坐下。将那份离婚协议轻轻放在桌角,
然后掏出手机,再次点开李威那条信息,屏幕朝上,推到书桌中央,
让那几行冰冷的文字再次暴露在父母眼前。“爸,妈,先冷静。
”我的声音在封闭的书房里显得异常清晰和稳定,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
“愤怒解决不了问题。这笔贷款,是我布的局。”父亲暴怒的眼神猛地一凝,
如同高速行驶的列车被强行扳动了道岔,硬生生拐了个方向。他撑在桌上的手微微松开,
身体僵住,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愕和困惑。“你…你布的局?
”他重复了一遍,语气是全然的不解。母亲也猛地抬起头,空洞的眼神聚焦在我脸上,
充满了茫然和一丝微弱的不敢置信的希望。“对。”我迎上父亲审视的目光,没有任何闪躲,
“从我发现徐芳和李威的事情开始,我就知道,仅仅离婚,远远不够。
以李威那种人的贪婪和徐芳的愚蠢,他们不会甘心只拿走一半财产。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从我身上榨取更多,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我的语速平稳,逻辑清晰,
像是在分析一个与我无关的商业案例。“李威,他那个所谓的‘金融服务公司’,
其实就是个空壳,专搞骗贷和非法集资,早就被盯上了,资金链随时会断。
他急需一大笔钱来填窟窿,或者跑路。”我顿了顿,
目光扫过桌上手机屏幕里“200万”那个刺眼的数字,“而徐芳,
就是他选中的、最完美的突破口和工具。她了解我们家,了解我的财务状况,更重要的是,
她够蠢,够贪婪,也够……狠。”“所以,”我微微吸了口气,眼神变得锐利,
“与其被动等着他们出招,不如主动给他们递一把‘刀’。这把刀,
就是这笔200万的‘经营贷款’。我利用了一些渠道,
故意让李威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并且让他相信,
通过徐芳的‘枕边风’和在我父母面前演苦情戏,可以彻底麻痹我,让我放松警惕,
甚至能影响我的决策,最终在他们设定的时间点,把这笔钱‘合理’地转出去,
或者……制造点‘意外’,让我失去处理这笔钱的能力。”“意外?!”母亲倒抽一口冷气,
声音带着剧烈的颤抖,“他们…他们真敢想…”“他们当然敢想,也敢做。
”我的声音冷了下去,“李威手上不干净,逼急了,没什么不敢。
徐芳被所谓的‘爱情’和贪婪冲昏了头,就是他的帮凶。”我看向父亲,“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