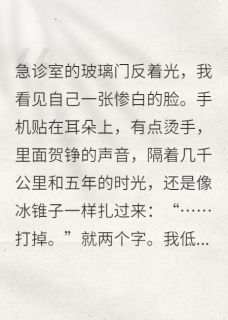由余浅生编写的热门小说带球跑后大佬他悔疯了,剧情非常的新颖,没有那么千篇一律,非常好看。小说精彩节选林晓家属在不在?”我猛地按掉电话,手心全是汗。家属?哪来的家属。肚子里这个的爹,刚才隔着电话,让他妈把他打掉呢。我叫……
章节预览
急诊室的玻璃门反着光,我看见自己一张惨白的脸。手机贴在耳朵上,有点烫手,
里面贺铮的声音,隔着几千公里和五年的时光,还是像冰锥子一样扎过来:“……打掉。
”就两个字。我低头,看着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四个月了,刚显怀。护士在喊:“林晓!
林晓家属在不在?”我猛地按掉电话,手心全是汗。家属?哪来的家属。肚子里这个的爹,
刚才隔着电话,让他妈把他打掉呢。我叫林晓。肚子里这个,
是我和贺铮分手前最后一点“纪念品”。那会儿,
他忙着跟他那个门当户对的青梅竹马培养感情,两家要联姻的消息满天飞。我呢?
我就是他见不得光、腻了随时能扔的地下情人。分手那天挺和平,他给了张卡,数额不小,
说是补偿。我接了,没矫情,转身就把他所有联系方式拉黑删除一条龙服务。
谁知道一个月后,我吐得昏天暗地,一查,中奖了。当时不是没犹豫过。拿着那张卡,
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生下来自己养?还是听贺铮刚才电话里那冷冰冰的两个字,处理掉?
我摸着肚子,里面那个小东西像是知道我在想它,轻轻拱了一下。就那么一下,
我眼泪唰地下来了。去他妈的贺铮,老娘自己的种,自己做主!我拿着那张卡,跑得飞快。
贺铮势力是大,但天大地大,真想藏起来,也不是不行。我找了个南方靠海的小城,不大,
但舒服。用那笔钱,盘了个小小的烘焙工作室,名字就叫“小满”。我肚子里这个,
小名叫满满,我希望他的人生,小满即可,不必太满,也别亏欠。满满生下来那天,
我一个人进的产房。痛得撕心裂肺的时候,脑子里全是贺铮那张冷漠的脸和他那句“打掉”。
这股恨意支撑着我,把满满生了下来。七斤二两,嗓门贼亮。护士把他抱到我怀里,
小小软软的一团,皱巴巴像个小老头,可那双眼睛,乌溜溜的,像极了贺铮。我抱着他,
又哭又笑。从此,我的世界,就只有我和这个小崽子了。日子过得飞快。
满满从软趴趴的小婴儿,长成了个能上房揭瓦的小魔王。我的“小满”工作室,
也从勉强糊口,到有了一小撮忠实的顾客。日子清贫,但踏实。满满就是我的命根子,
我的小太阳。满满五岁那年,春天。他突然蔫了,老说腿疼,开始以为是生长痛,没太在意。
后来疼得晚上睡不着,小脸煞白,还发起低烧。带去社区医院看,医生皱着眉看了半天,
让我赶紧去市里大医院查查。结果像晴天霹雳。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那几个字砸下来,
我眼前一黑,差点当场栽倒。医生后面说了什么治疗方案、预后、费用……我耳朵里嗡嗡响,
只抓住几个词:化疗、骨髓移植、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我的“小满”工作室,
一年到头也就挣个十几万,刚够我们娘俩在小城温饱。几十万?上百万?
我拿命也填不上这个窟窿。看着病床上因为打了止疼针暂时睡着的满满,小脸瘦了一圈,
我的心被撕成了碎片。回老家那个大城市,是唯一的选择。那里有最好的儿童血液科,
更重要的是,我必须找到贺铮。他是满满的生物学父亲,是骨髓配型成功率最高的希望,
也是唯一能拿出这笔天文数字医疗费的人。为了满满,什么尊严,什么过往的恨,
我都得咽下去。我把工作室低价盘了出去,带着全部家当和病恹恹的满满,
坐上了北上的火车。五年了,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空气都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压迫感。
安顿好满满住进医院,开始痛苦的化疗。看着针扎进他细小的血管,他疼得浑身发抖,
咬着嘴唇不哭出声,只会用那双酷似贺铮的眼睛看着我,小声说:“妈妈,满满勇敢。
”我背过身,指甲掐进掌心,才没让眼泪决堤。找贺铮,成了比化疗更折磨我的事。
他那个级别的圈子,不是我一个消失五年的人能轻易摸进去的。我像个无头苍蝇,
在他以前常去的几个高端会所、公司楼下蹲守,毫无所获。他换了车,换了司机,
连常去的餐厅都换了。我甚至鼓起勇气,试图联系他那个“青梅竹马”赵**,电话打通,
我刚报出名字,对方冷笑一声就挂了,再打过去就是忙音。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
化疗费、住院费、各种检查费……我那点存款,撑不了几天。信用卡刷爆了,
能借的亲戚朋友借了个遍,杯水车薪。巨大的绝望像冰冷的潮水,一点点淹没我。那天下午,
满满刚做完骨穿,哭得嗓子都哑了,好不容易睡着。我坐在医院楼下冰冷的长椅上,
翻着手机通讯录,一片空白。天阴沉沉的,压得人喘不过气。鬼使神差地,
我拨通了一个烂熟于心、却五年没敢碰的号码。“嘟…嘟…”每一声都像敲在我心尖上。
电话居然通了!一个低沉的、带着点不耐烦的男声传来:“哪位?”是贺铮!
声音比五年前更沉,更有压迫感。我的手抖得厉害,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五年了,
我以为自己恨他入骨,可听到他声音的这一刻,巨大的委屈和恐惧瞬间冲垮了我。“说话。
”他语气更冷。“贺铮…”我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带着浓重的哭腔,“是我…林晓。
”电话那头瞬间死寂。过了好几秒,他像是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冰冷刺骨,
带着浓浓的嘲讽和厌恶:“林晓?你还敢给我打电话?消失五年,钱花完了?
”他以为我是来要钱的!巨大的屈辱感让我浑身发冷。我死死咬着嘴唇,尝到了血腥味,
才压下那股想把电话摔掉的冲动。为了满满,林晓,你忍!“不是…贺铮,
我…”我深吸一口气,指甲深深陷进掌心肉里,“我需要你帮忙。救命…救救我们的孩子。
”“什么孩子?”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嗤笑一声,“林晓,你疯了吧?
当年分手费给得清清楚楚,我们早就两清了。少拿这种下三滥的借口来纠缠我,你这种女人,
我见多了。”“我没有骗你!是真的!”我急得眼泪疯狂往下掉,“他叫满满,五岁了,
他病了,很严重的病!白血病!他需要骨髓移植,需要钱救命!贺铮,他是你儿子!亲生的!
”“够了!”贺铮厉声打断我,声音里是毫不掩饰的暴怒和鄙夷,“编故事也编得像样点!
五年前分手的时候你怎么不说?现在缺钱了,想起弄个野种来讹诈我?林晓,
你真是让我恶心透了!别再来烦我!”“嘟…嘟…嘟…”忙音传来,像冰冷的刀子。
我握着手机,站在人来人往的医院门口,浑身冰凉,如坠冰窟。阳光刺眼,
我却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他不信。他骂满满是野种。他说我恶心。最后一丝希望,
被他亲手掐灭了。接下来的日子,是地狱。贺铮那边彻底没了指望。
高昂的医药费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催缴费用的单子一张接一张。
我白天在医院照顾满满,看着他被化疗折磨得不成样子,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晚上,我就出去找活干。能做什么?我以前那点烘焙手艺,
在这种大城市,根本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时间也不允许。我只能去便利店做通宵的夜班,
去凌晨的菜市场帮人搬货,去写字楼做按小时结算的保洁。一天睡不到三四个小时。
累到极致的时候,我就坐在满满病床边,握着他插着留置针的小手,
看着他睡梦中偶尔因为疼痛皱起的眉头。贺铮那张冷酷厌恶的脸就会浮现在我眼前。
恨意像藤蔓一样疯狂滋长,缠绕着我的心。凭什么?凭什么他锦衣玉食,高高在上,
而我的满满却要承受这种痛苦?凭什么他不信?凭什么他说满满是野种?这恨意支撑着我,
像一根绷紧到极致的弦。那天,满满的白细胞低得吓人,医生下了病危通知,
必须立刻输血小板,否则有颅内出血的危险。可账上的钱,连一支进口升白针都买不起了。
我翻遍了所有的卡,所有的支付软件,余额全是刺眼的零。我冲到医院楼下的ATM机,
把我最后一张银行卡**去。那是贺铮当年给我的分手费卡,后来跑路时我把钱转走了,
卡一直留着,像个耻辱的纪念。余额显示:3.21元。巨大的绝望和恨意瞬间吞噬了我。
我疯了一样,对着冰冷的机器屏幕,用尽全身力气嘶吼:“贺铮!你**!王八蛋!
那是你儿子!你亲儿子!他要死了!你满意了吗?!你满意了吗?!
”声音在空旷的自助银行里回荡,带着泣血的绝望和疯狂。喊完,
我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瘫软在冰冷的机器旁,抱着膝盖,嚎啕大哭。我不知道的是,
医院大厅的VIP电梯门,在那一刻刚好打开。贺铮一身剪裁精良的深灰色西装,
被几个同样衣冠楚楚的人簇拥着走出来。他是来这家医院谈一笔高端医疗设备投资的合作。
我绝望的嘶吼和痛哭,像惊雷一样,清晰地砸进了他的耳朵里。他脚步猛地顿住,
锐利的目光穿透人群,精准地锁定了自助银行里那个蜷缩在地上、哭得浑身发抖的瘦弱身影。
五年不见,她变得几乎认不出来。苍白,憔悴,瘦得脱了形,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枯叶。
可那绝望的哭喊声,那刻骨的恨意,却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心口一窒。“林晓?
”他身边的助理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低声确认,
“好像是她…她刚才喊…”贺铮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下颌线绷得死紧。他没有说话,
也没有动,只是死死地盯着那个方向,眼神复杂得如同风暴过境。助理试探地问:“贺总?
合作方还在等…”贺铮抬手,制止了他后面的话。他迈开长腿,径直朝自助银行走去。
皮鞋踩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冰冷而沉重的回响。我哭得眼前发黑,
根本没注意到有人靠近。直到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下来,挡住了头顶惨白的光线。
一股熟悉的、冷冽的雪松混合着烟草的凛冽气息,强势地侵入我的感官。我猛地抬头。
贺铮就站在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五年时光沉淀,他身上那股上位者的压迫感更重了,
眼神深邃得像寒潭,此刻正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惊涛骇浪。他脸上没什么表情,
但紧抿的唇线和绷紧的下颌,泄露了他此刻绝不平静的内心。“你刚才说什么?
”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种极力压抑的紧绷,“谁要死了?
”巨大的震惊和屈辱感瞬间攫住了我。我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以如此狼狈不堪的姿态,
再次见到他。刚才的嘶吼用尽了我所有力气,此刻只剩下冰冷的恨意和麻木。
我扶着冰冷的ATM机,挣扎着想站起来,腿却软得不听使唤。我索性不站了,仰着头,
通红的眼睛死死瞪着他,嘴角扯出一个极其难看的、充满恨意的笑:“贺总?真巧啊。
来看我笑话吗?看我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趴在这里?满意了?你贺大总裁高高在上,
踩死我们母子,比踩死蚂蚁还容易!你儿子要死了!听清楚了吗?
那个被你骂作‘野种’的孩子!他快死了!你开心了?滚!你给我滚!
”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吼出那个“滚”字,胸口剧烈起伏,眼前阵阵发黑。贺铮的脸色,
在我那句“你儿子要死了”出口时,彻底沉了下去,阴鸷得可怕。
他身后的助理和保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但他没有动,也没有发怒,
只是眼神锐利如刀地钉在我脸上,似乎在分辨我话里的真假和疯狂的程度。
几秒钟死寂的沉默,空气凝滞得让人窒息。“他在哪?”贺铮的声音冷得像淬了冰,
不容置疑。我愣了一下,随即是更大的愤怒和悲哀。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想怎么样?
亲自去确认一下那个“野种”是不是真的快死了,好满足他那点可悲的掌控欲?“关你屁事!
”我嘶声骂道,“贺铮,收起你那套假惺惺!我们母子是死是活,跟你没关系!
滚回你的金窝银窝里去!”贺铮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他不再看我,直接转头,
对身后噤若寒蝉的助理厉声道:“查!五分钟内,
我要知道这家医院所有叫林晓的患儿住院记录!立刻!”助理吓得一个激灵:“是!贺总!
”立刻掏出手机跑到一边。“你干什么!”我慌了,扑过去想阻拦,“贺铮!你没权利!
你离我儿子远点!”贺铮一把抓住我挥舞过来的手腕。他的手劲极大,捏得我骨头生疼,
冰冷的目光带着绝对的压迫感:“林晓,你最好祈祷你说的是真的。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
”他甩开我的手,力道之大让我踉跄着撞在ATM机上。不到三分钟,助理就跑了回来,
脸色有些发白,手里拿着手机:“贺总,查到了!在…在七楼儿童血液科,重症监护区,
林满满…五岁…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刚下了病危通知,急需输血小板,
但…家属账上欠费严重…”贺铮的脸色,在听到“病危通知”四个字时,骤然剧变。
他猛地转头看向我,那眼神里翻涌的情绪复杂得惊人,有震惊,有难以置信,
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恐慌?“带路!”他对着助理低吼一声,再没看我,
大步流星地冲向电梯。我顾不得手腕的疼痛和满心的恨意,连滚爬爬地追了上去。
我不能让他靠近满满!谁知道他会对我的孩子做什么!电梯直达七楼。贺铮走得飞快,
助理小跑着才能跟上。我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心提到了嗓子眼。重症监护区门口,
气氛压抑。护士看到我们一行人气势汹汹地过来,有点紧张。贺铮根本不理会,
他的目光透过玻璃门,精准地锁定了里面那张小小的病床。
满满小小的身体陷在白色的被子里,几乎看不见。他戴着氧气面罩,小脸惨白得像纸,
头发因为化疗掉得稀稀拉拉,露着头皮。胳膊上、脚上插着好几根管子,
旁边的心电监护仪发出规律而微弱的滴滴声。贺铮的脚步,在玻璃门前猛地停住了。
他高大的身躯,第一次,显得有些僵硬。他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隔着玻璃,
死死地看着病床上那个脆弱得仿佛一碰即碎的小生命。时间仿佛凝固了。
我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看着他宽阔却僵硬的背影,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疼得无法呼吸。满满…我的满满…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只有几秒,也许有一个世纪那么长。
贺铮缓缓地、极其缓慢地转过身。他的脸色依旧冷硬,但那双深邃的眼睛里,
有什么东西彻底碎裂了。震惊、茫然、一种铺天盖地的恐慌,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痛楚?
他看着我,眼神不再是刚才的冰冷和审视,
而是像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让他无法理解的存在。
“他…”贺铮的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声音哑得不成样子,
带着一种他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他长得…像我。”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带着一种被铁证砸中般的恍惚和…确认。我所有的恨意、委屈、恐惧,
在他这句沙哑的“像我”面前,轰然崩塌。眼泪决堤而出,我再也支撑不住,
靠着冰冷的墙壁滑坐到地上,捂着脸,失声痛哭。
自支撑的艰辛、被误解被辱骂的屈辱、看着孩子受苦的无助…所有的情绪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贺铮没有动。他就站在那里,听着我撕心裂肺的哭声,
看着玻璃门内那个和他血脉相连却命悬一线的孩子。他脸上的冷硬面具,
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那是一种近乎空白的茫然和…无措。助理小心翼翼地靠近,
递上一份文件:“贺总,紧急调用的血小板和最好的进口升白针马上送到。另外,
这是医院刚刚收到的…亲子鉴定加急报告,结果…出来了。
”他看了一眼瘫坐在地上痛哭的我,声音更低,“支持…贺铮先生是林满满的生物学父亲。
”那份薄薄的报告,像有千斤重。贺铮没有接,他的目光死死盯着报告结论那一栏的几个字。
助理的手僵在半空。空气死寂。只有我的哭声,压抑而绝望地回荡在走廊里。许久,
贺铮才极其缓慢地抬起手,接过了那份报告。他的手指骨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他没有翻开看结论,只是死死捏着那份报告,指关节捏得咔咔作响,
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他猛地转过头,不再看病房,不再看报告,
而是死死地盯着瘫坐在地上的我。那眼神,不再是冰冷,不再是厌恶,
而是翻涌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几乎要将他吞噬的情绪——震惊、愤怒(对自己?
)、难以置信,还有浓烈的、几乎化为实质的悔恨和…恐慌。“林晓,
”他的声音嘶哑得像是砂纸摩擦,“你…好样的。”这句话,不知道是咬牙切齿的恨,
还是痛彻心扉的悔。他说完,不再看我,猛地转身,对着助理和匆匆赶来的医院领导,
声音冷厉如刀,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用最好的药!最好的医生!钱不是问题!我要他活!
必须活!”接下来的日子,像一场混乱而压抑的梦。钱,不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