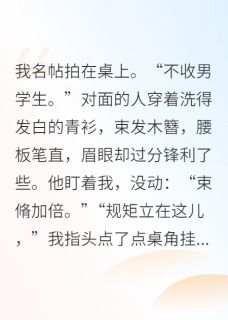古代开女子书院,王爷他来当学生描绘了萧珩山长的一段异世界冒险之旅。他身世神秘,被认为是命运的守护者。十六爪章鱼巧妙地刻画了每个角色的性格和动机,小说中充满了紧张、悬疑和奇幻元素。精彩的情节将带领读者穿越时空,探索那些隐藏在黑暗背后的秘密。
章节预览
我名帖拍在桌上。“不收男学生。”对面的人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衫,束发木簪,腰板笔直,
眉眼却过分锋利了些。他盯着我,没动:“束脩加倍。”“规矩立在这儿,
”我指头点了点桌角挂的木牌,上面刻着“梧桐书院,仅收女学生”几个字,
“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守。”后面排队的女学生开始窃窃私语。“束脩三倍。”他又说,
声音不高,但清晰地压过了所有议论。我眼皮都没抬,朝旁边喊:“阿杏,送客。下一个!
”书院管事阿杏立刻上前,板着脸:“这位公子,请吧。”他站着没动,
目光沉沉落在我脸上,像带着重量。“洛山长,”他终于开口,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冷硬,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我求学之心甚诚。”我这才抬眼,仔细打量他。手指骨节分明,
虎口有茧,那是长期握刀或握剑留下的。脖颈处的皮肤颜色与露出的手腕截然不同,
显然是常年风吹日晒的印记,与这身刻意做旧的寒酸衣衫格格不入。
更别提那股子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再怎么伪装也藏不住的迫人气势。“心诚?”我嗤笑一声,
声音不大,只够他听见,“那你该先学学如何藏住指缝里的金粉,
还有……喉结下那道没易容好的旧疤。”他瞳孔猛地一缩。**回椅背,声音扬起来,
对着后面看热闹的女学生们,清晰地说道:“梧桐书院,只教女子识字明理,只收女子束脩。
这位……公子,您请回。再纠缠,我只好报官,说有人强闯女学,意图不轨了。
”后面排队的姑娘们发出一阵低低的哄笑,有人胆子大的还附和:“就是!快走吧!
”他脸色沉了下来,眼神锐利得像刀子,在我脸上剐过。最终,他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
青衫背影在春日暖阳下,竟透出几分萧索冷意。阿杏凑过来,小脸发白:“山长,
那人……看着不像善茬。眼神吓人。”我端起凉透的茶喝了一口:“怕什么。开门办学,
讲的就是规矩。他再横,还能砸了我的书院不成?”话是这么说,我心里也清楚,
那人绝非普通寒门学子。那份气度,那份被戳穿身份时的瞬间反应,非富即贵,
甚至……可能沾着权柄。麻烦,恐怕才刚开始。果然,麻烦第二天就来了。
不是明刀明枪的砸场子。是一群穿着体面绸衫、管事模样的人,
抬着好几个沉甸甸的红木箱子,直接堵在了书院门口。领头的是个山羊胡,
说话滴水不漏:“洛山长,我家主人仰慕书院清名,特命我等送来薄礼,
为书院添置些笔墨书籍。另外……”他顿了顿,递上一张洒金名帖,“主人府中几位**,
亦想拜入山长门下,束脩按最高规格奉上,还望山长行个方便。”我瞥了一眼那帖子。
落款龙飞凤舞,只有一个字——“珩”。珩,美玉,亦指佩玉之横玉。寻常人家,
谁敢单用此字?阿杏在我身后吸了口冷气,显然也想到了什么。我接过帖子,指尖冰凉,
脸上却挤出一点笑:“贵主人厚爱,洛云漪愧不敢当。只是书院规矩,只收女学生。
贵府千金自然符合,欢迎之至。至于这些厚礼……”我示意阿杏,“书院清寒,
受不起如此大礼,请抬回去。”山羊胡的笑容僵在脸上:“洛山长,
这……”“规矩就是规矩。”我把名帖塞回他手里,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请回吧。
贵府千金若要入学,按正常流程递名帖即可。”箱子被原封不动地抬走了。
山羊胡走时的眼神,比昨天那青衫人更冷。接下来的日子,风平浪静。
那几位“珩”府的**也没递名帖来。我以为这事就算过了。直到半个月后,书院正式开课。
我教的是经义。正讲到“君子不器”,窗外忽然传来一阵骚动。夹杂着女学生的惊呼。
我皱眉走出去。只见书院后院那堵不算太高的围墙下,一个青衫身影正利落地拍着身上的灰。
正是那天被我赶走的“寒门学子”。他竟翻墙进来了!“你!”阿杏气得脸通红,指着他,
“你好大的胆子!敢翻墙私闯女学!”他站直身体,神色坦然,
仿佛只是从大门走进来一般:“求学心切,不得已出此下策。山长,我愿受罚,
只求一个旁听的机会。”女学生们围在不远处,又是惊又是奇,交头接耳。我看着他,
一股邪火蹭地冒上来。权势压人不行,改玩无赖了?真当我是泥捏的?“受罚?”我冷笑,
“行。阿杏,去拿针线笸箩来。”阿杏一愣,不明所以,但还是飞快跑去了。很快,
一个装满各色丝线和绣花针的笸箩被端了过来。我往他面前一递,声音平静无波:“想旁听?
可以。拿着,去那边廊下坐着。今日散学前,绣出一朵完整的莲花。绣得出,
明日准你坐最后一排。绣不出,自己从哪儿翻进来的,再从哪儿翻出去。”空气瞬间凝固。
女学生们全都傻了眼,随即有人忍不住捂嘴笑起来。让一个大男人,
还是这样一个气势迫人的大男人……绣花?他盯着那笸箩,脸上一贯的平静终于裂开一道缝,
眼神复杂地看向我,有错愕,有难以置信,甚至有一丝……被羞辱的薄怒。
“山长……”他开口,声音有些发紧。“怎么?”我挑眉,“规矩是我定的。翻墙的惩罚,
也是你该受的。绣花,或者立刻滚蛋。选吧。”四目相对。他眼底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情绪,
最终,归于一片深沉的墨色。他伸手,接过了那个与他气质格格不入的针线笸箩。“好。
”他抱着笸箩,在众目睽睽之下,真的走到廊下角落,找了个石墩坐下。
高大的身躯蜷在小小的石墩上,低着头,开始笨拙地跟那些细小的针线较劲。阳光透过廊檐,
在他紧绷的侧脸上投下明暗的光影。那画面,说不出的诡异又……滑稽。
女学生们想笑又不敢笑,一个个憋得小脸通红,偷偷瞄着廊下。
我面无表情地走回课堂:“继续上课,‘君子不器’……”整整一个下午,
廊下那人都在跟针线搏斗。期间,我听到不止一次细微的抽气声,大概是针扎了手。散学时,
他面前的石墩上,只留下了一小块被戳得千疮百孔、染了几点可疑暗红的素白绸布。
别说莲花,连个像样的形状都没有。他站起身,将那团惨不忍睹的“作品”递给我,
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指尖残留着被针扎出的细小血点。“明日,我坐最后一排。”他说完,
转身就走,依旧是从那堵墙翻了出去。我看着那团破布,随手丢给阿杏:“烧了。
”阿杏咋舌:“山长,他……他明天真还来啊?”“来就来。”我转身回屋,“最后一排,
给他留着。”第二天,他果然来了。没翻墙,不知用了什么法子,竟说服了守门的老仆,
正大光明地走了进来。依旧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衫,木簪束发,只是左手食指和中指上,
多了几个显眼的针眼。他目不斜视,径直走到最后一排角落的空位坐下,拿出笔墨纸砚,
姿态端正,仿佛自己真是个来求学的普通书生。课堂上,女学生们频频回头偷看,气氛微妙。
我讲《诗经》里的《关雎》。讲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时,故意停顿,目光扫过全场,
最后落在他脸上。“此句,可有哪位学生能解其意?”没人敢应声。都知道这是个送命题。
我点了一个前排素来伶俐的姑娘:“玉兰,你来说说。”玉兰站起来,
脸微红:“是说……贤良美好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嗯,解其字面,尚可。
”我点点头,话锋一转,“然则,君子所求,仅是‘配偶’二字乎?所求者,是琴瑟和鸣,
是志同道合,是并肩观天地,而非圈养闺阁,只知绣花描眉。若只以‘配偶’视之,
与豢养金丝雀何异?此等‘逑’,非君子所求,乃俗物所求也!”我的声音清朗,
在安静的课堂里回荡。女学生们眼睛亮了起来,若有所思。最后一排,他握着笔的手顿住了。
墨点滴落在纸上,晕开一小团黑。他抬起眼,目光穿过整个课堂,直直落在我身上。
那眼神很深,像幽潭,不再有昨天的薄怒或窘迫,而是带着一种审视,一种……探究。
下课铃响。我收拾书卷。他站起身,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立刻离开,
而是穿过窃窃私语的人群,径直走到我的讲案前。“山长今日所言,振聋发聩。”他开口,
声音低沉,“‘并肩观天地’……此等女子,何处可寻?”我抬眼看他:“梧桐书院,
正在教。不过,靖王爷,”我压低了声音,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您府上佳丽三千,
何必来此寻?”他瞳孔骤然收缩,周身那股刻意收敛的气势瞬间泄露出一丝,
如同利刃出鞘一瞬的寒芒。他盯着我,沉默了片刻,忽然极轻地笑了一下,那笑意未达眼底。
“洛山长好眼力。看来本王这点微末伎俩,在山长面前,不过是跳梁小丑。”他承认了。
靖王萧珩。当今圣上的幼弟,手握重兵,权倾朝野。
一个传说中冷酷铁血、不近女色的煞神王爷。“王爷谬赞。”我神色不变,
“只是王爷翻墙的手艺,略显生疏。绣花的功夫,更是惨不忍睹。下次若还想潜入,
不妨换个法子。”他眼底闪过一丝异色,似乎没料到我敢如此直接地揶揄他。“山长对本王,
似乎颇有成见?”“不敢。”我抱起书卷,“只是王爷身份尊贵,
屈尊降贵来我这小小的女子书院,所求为何?总不会真是为了听我讲《关雎》,学绣花吧?
”“若本王说,”他微微俯身,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种迫人的压力,
“正是为了山长口中那‘并肩观天地’的女子呢?”距离太近,
我能闻到他身上清冽的松墨气息,混着极淡的、属于兵戈的铁锈味。我退后一步,拉开距离,
直视他深邃的眼:“那王爷更该明白,此等女子,绝非靠强权可以圈养,更不会甘为附庸。
梧桐书院,教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爷若想‘逑’,请先学会尊重二字。”说完,
我不再看他,转身离开。他在我身后,许久没有动。自那日挑明身份后,
萧珩反而来得更勤了。依旧坐最后一排,听课,记笔记,姿态无可挑剔。
他不再刻意伪装寒酸,那身青衫料子明显好了许多,木簪也换成了温润的玉簪,
只是整个人依旧沉默寡言,像一尊俊美却冰冷的石雕。书院里关于他的议论从未停歇。
有说他痴迷山长美色,不顾身份死缠烂打的;有说他身负皇命,
暗中调查书院的;更有离谱的,说他身患隐疾,唯有书院清气可医。对这些,我一概不理。
讲课,授业,管理书院杂务,日子按部就班。直到那天,教习女红的陈娘子告假,
我临时顶替。课上教的是双面绣的入门针法。我坐在绣架前示范,底下的女学生们学得认真。
萧珩坐在最后一排,面前摊开的是《策论》,目光却越过书页,落在我穿针引线的手指上。
“双面绣之要诀,在于‘藏’。”我一边讲解,一边运针,“针脚要细密均匀,
线头要藏匿于绣线之中,翻转之后,方能两面光洁如一,不见瑕疵。如同做人行事,
内里功夫做足了,表相自然圆融通透,经得起翻转细看。”我刻意放慢了动作,
让针线在绷紧的素缎上穿梭。余光瞥见萧珩放下了手中的书,看得专注,眉头微蹙,
似乎在思索什么。下课后,我正收拾绣架上的丝线。一个高大身影笼罩下来。“山长,
”萧珩的声音在头顶响起,“这双面绣……当真两面皆无瑕疵?”我抬头,
对上他探究的目光:“王爷想试试?”他沉默片刻,竟真的伸出了手:“可否借针线一观?
”我有些意外,还是将手中的细针和一小段丝线递给他。他接过去,
指腹捻着那根细如发丝的绣花针,又看了看光滑的丝线,眉头锁得更紧。他学着我的样子,
笨拙地试图将线穿过针鼻。那动作生硬得可笑,与他握笔批阅军报时的沉稳判若两人。
试了几次,线头都散了。他显然有些烦躁,手指用力。“啪。”一声极轻微的脆响。针断了。
半截细针落在地上,闪着冷光。他捏着剩下的半截针尾,僵在那里,
看着自己指尖被断口划出的一道细细血痕,眼神晦暗不明。我看着他指尖沁出的那点殷红,
忽然觉得这权倾天下的王爷,此刻竟有些……笨拙的可怜。“看来王爷的指力,
”我淡淡开口,递过去一块干净的素帕,“更适合握刀。”他盯着那帕子,没接。
反而抬眼看向我,眼神锐利:“山长方才说,‘藏’。藏针脚,藏线头。那人心呢?
是否也能藏得天衣无缝?”我收回帕子:“人心难测,自然无法尽藏。但求行事光明,
无愧于心,又何须刻意去藏?藏得了一时,藏不了一世。王爷在军中多年,当知‘虚则实之,
实则虚之’的道理。藏与露,存乎一心,过犹不及。”他深深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将断针放在我的绣架上,转身大步离去。那之后,他消失了几天。书院里清静不少,
女学生们还有些怅然若失。阿杏嘀咕:“山长,您把王爷气跑了?”我正核对账目,
头也不抬:“跑了更好。省心。”然而,清静没持续多久。更大的风暴来了。
一封盖着凤印的懿旨,由一队气势汹汹的宫中内侍,直接送到了书院正堂。
为首的内侍总管嗓音尖利,趾高气扬:“太后懿旨!梧桐书院山长洛云漪接旨!
”堂内所有女学生、教习娘子、仆役,齐刷刷跪了一地,人人脸色煞白。太后!
那可是当今天子生母,后宫最尊贵的女人!我深吸一口气,跪在最前面:“民女洛云漪接旨。
”“奉天承运,太后懿旨:查梧桐书院山长洛云漪,身为女子,不安于室,妄开女学,
混淆阴阳,蛊惑人心。其所授之学,悖逆伦常,动摇国本,更兼私纳外男,秽乱学宫,
败坏风气!实乃礼教之蠹虫,女子之耻尤!着即日起,查封梧桐书院,遣散所有学生,
山长洛云漪,押入宗人府,听候发落!
——”“秽乱学宫”、“礼教蠹虫”、“女子耻尤”……一个个恶毒的词语像淬了毒的冰锥,
狠狠扎进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女学生们吓得瑟瑟发抖,有胆小的已经低声啜泣起来。
阿杏跪在我身边,浑身都在颤。内侍总管念完,将明黄的懿旨一卷,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嘴角挂着刻薄的笑:“洛山长,接旨吧?还是想抗旨?”整个正堂,死一般的寂静。
空气沉重得让人窒息。我抬起头,看着那卷象征最高权威的懿旨,心一点点沉下去,
沉到冰冷的谷底。太后的刀,终于落下来了。罪名如此荒谬,却又如此致命。封院,抓人。
她不仅要毁了我的书院,更要彻底毁掉我这个人,以及我背后所代表的“离经叛道”。
“民女,”我开口,声音出乎自己意料的平静,“接旨。”两个字,重若千钧。
正堂里压抑的哭声瞬间大了起来。“不过,”我站起身,没有去接那懿旨,
目光直视着内侍总管,“在查封之前,容民女问总管大人一句。懿旨所言‘私纳外男,
秽乱学宫’,所指何人?可有实据?若无实据,便是污蔑。民女虽微贱,亦知国法昭昭,
诬告当反坐!太后娘娘母仪天下,明察秋毫,断不会仅凭风闻便定人死罪!请总管大人明示!
”我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带着一股豁出去的决绝,在寂静的正堂里回荡。
内侍总管显然没料到我敢当众质问,脸色一沉,厉声道:“大胆!太后懿旨,岂容你置喙?
证据?哼,靖王爷在你书院出入多日,人所共见!你一个未嫁女子,私留外男于女学重地,
不是秽乱,是什么?还敢狡辩!来人——”“慢着!”一声冷喝,如同惊雷,
骤然在书院大门外炸响!沉重的朱漆大门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阳光倾泻而入,勾勒出一个挺拔如松、身着玄色亲王常服的身影。萧珩!
他大步流星地走进来,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周身散发着骇人的戾气。他身后,
跟着两队身着玄甲、腰挎长刀的王府亲卫,铁甲森然,步伐整齐划一,
瞬间将那群宫中内侍隐隐围住,强大的压迫感让整个正堂的温度骤降。内侍总管看清来人,
脸色剧变,嚣张气焰瞬间矮了半截,慌忙躬身行礼:“老奴参见靖王殿下!
殿下千岁……”萧珩看都没看他一眼,鹰隼般的目光直接锁定我,在我脸上停留一瞬,
确认无恙后,才转向那内侍总管,声音冷得像冰碴子:“本王在何处出入,
何时轮到你一个阉奴置喙?又何时轮到后宫,对本王的行踪指手画脚?”他一步步逼近,
那内侍总管吓得连连后退,冷汗涔涔:“殿下息怒!
老奴……老奴只是奉太后懿旨行事……”“懿旨?”萧珩冷笑一声,
劈手夺过总管手里那卷明黄绸缎,看也不看,手腕一抖!“刺啦——!
”刺耳的撕裂声响彻正堂。那卷代表着至高无上权威的太后懿旨,竟被他当众,
生生撕成了两半!碎片飘落在地。全场死寂!落针可闻!所有人都惊呆了,包括我。
撕毁懿旨!这是何等的大逆不道!形同造反!内侍总管吓得魂飞魄散,腿一软,
直接瘫跪在地,面无人色:“王、王爷!您……您这是……抗旨……大逆……”“抗旨?
”萧珩将手里的碎绸随手一扔,眼神睥睨,带着一种久居上位、生杀予夺的冷酷,
“回去告诉太后娘娘,本王在梧桐书院,是奉圣上口谕,体察民情,暗访京中教化。
洛山长才学出众,书院管理有方,实乃女子教化之楷模!若有人敢污蔑功臣,构陷本王,
休怪本王……不念宫闱情分!”他最后几个字,说得极慢,字字如刀,
带着毫不掩饰的杀伐之气。那内侍总管瘫在地上,抖如筛糠,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萧珩不再看他,目光转向我,那眼中的冰寒稍褪,语气依旧冷硬:“洛山长受惊了。
本王在此,倒要看看,谁敢动梧桐书院一草一木!”他扫视全场,目光所及,
无人敢与之对视。他带来的王府亲卫齐声应诺:“喏!”声震屋瓦。
瘫软的内侍总管被王府侍卫像拖死狗一样架了出去,
那群之前还耀武扬威的宫中内侍也灰溜溜地跟着跑了,连地上的懿旨碎片都没敢捡。
正堂里依旧一片死寂。女学生们惊魂未定,看着地上那刺眼的明黄碎片,
又看看如战神般矗立在那里的玄衣王爷,眼神充满了敬畏和茫然。萧珩转向我,
脸色依旧冷峻,声音却缓和了些许:“山长,可有受伤?”我摇摇头,心绪复杂难言。
震惊于他撕毁懿旨的疯狂举动,更困惑于他那句“奉圣上口谕”的真假。他这是在赌,
赌太后不敢真的和他撕破脸,赌皇帝会默许他这次的“抗旨”。“多谢王爷解围。
”我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维持着表面的平静。他深深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只留下一句:“书院照旧开课。本王的人,会守在外面。”便带着亲卫,如来时一般,
大步离开了。一场灭顶之灾,因他雷霆万钧的闯入和那惊天一撕,暂时消弭于无形。
那撕碎的懿旨碎片,被阿杏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锁进了箱底。没人敢提,但所有人都知道,
那裂痕已经存在。梧桐书院和靖王萧珩的名字,以一种极其震撼的方式,被捆绑在了一起。
风波看似平息,暗流却更加汹涌。萧珩不再只是旁听。他开始插手书院的事务。
有时是送来一批珍贵的孤本典籍,
说是“充实书院藏书”;有时是调拨王府的护卫在书院外围巡逻,
美其名曰“维护清静”;甚至有一次,他直接带人,把书院后院那堵不太高的围墙,
加高了三尺,还砌上了光滑的青砖!我站在焕然一新的高墙下,看着那光溜溜的墙面,
哭笑不得。他这防谁翻墙呢?防他自己吗?“王爷这是何意?”我问他。他负手站在墙下,
一本正经:“书院重地,自当壁垒森严,以防宵小。”眼神却若有若无地瞟过我。我无语。
他不仅管墙,还管人。书院里有个叫婉娘的姑娘,家道中落才来求学,性子有些怯懦。
她父亲是个嗜赌的浑人,不知怎么打听到女儿在书院,竟跑来闹事,堵在门口要钱,
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婉娘吓得躲在房里哭。我刚要出去处理,阿杏气喘吁吁跑进来:“山长!
不用去了!靖王爷……王爷他……”我赶到门口时,只见婉娘那个五大三粗的爹,
被两个王府侍卫反剪着手臂按跪在地上,脸贴着冰冷的石板,嘴里塞了块破布,
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眼神惊恐地看着几步外负手而立的萧珩。萧珩面无表情,声音不高,
却带着令人胆寒的威压:“书院清静之地,岂容泼皮喧哗?此人惊扰学生,勒索钱财,按律,
杖三十,枷号三日。拖走。”“是!”侍卫领命,像拖死狗一样把瘫软的赌鬼拖走了。
围观的街坊邻居噤若寒蝉。婉娘红着眼睛出来,对着萧珩就要下跪。萧珩抬手虚扶了一下,
语气平淡:“安心读书。此等无赖,再不会来扰你。”他处理完,目光扫过我,微微颔首,
便转身走了。留下一个冷酷又……莫名令人心安的背影。类似的事情接二连三。
有地痞想来书院附近收保护费的,
被他的人打断了腿;有嫉妒书院生源、散布流言说书院女子不洁的酸腐文人,
被他当街斥责得哑口无言,灰溜溜遁走。不知不觉间,靖王府的势力,像一张无形的大网,
悄然笼罩在梧桐书院周围,挡住了外界的风刀霜剑。书院的教学秩序,
反而前所未有地安稳起来。女学生们对这位冷面王爷的态度,也悄然转变。
从最初的敬畏害怕,到好奇观望,再到如今,竟隐隐生出几分依赖和……崇拜?我冷眼旁观。
不得不承认,他的存在,确实为书院解决了许多我难以应付的麻烦。但这绝非长久之计。
依附于强权,本身就是对“独立”二字的讽刺。更何况,他撕毁懿旨的举动,
无异于在悬崖边跳舞。太后那边,绝不会善罢甘休。果然,平静的水面下,暗礁浮现。一日,
我正批阅学生的策论,阿杏慌慌张张跑进来,脸色惨白:“山长!不好了!
玉兰……玉兰被家里人强行带走了!说是……说是要送她入宫参加采选!”玉兰?
我心头一沉。那是书院里最聪慧、最有主见的一个姑娘,父亲是个六品京官,官位不高,
却最是趋炎附势。他之前就对女儿在梧桐书院读书颇有微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该早早嫁人。如今竟要送女入宫?“什么时候的事?”我猛地站起。“就刚才!玉兰不愿意,
被她爹带来的家丁硬拖上马车的!她哭喊着挣扎,被堵了嘴……”阿杏急得快哭了,“山长,
玉兰不想入宫啊!她说过想考女官,想自己立业的!”一股怒火直冲头顶。入宫采选?
说是飞上枝头,实则不过是把女儿当作攀附权贵的筹码,
送入那吃人不吐骨头的深宫去搏一个虚无缥缈的前程!葬送的是玉兰的一生!“备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