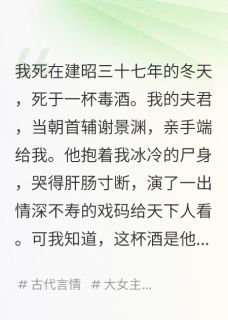知名网文写手“玲珑砚磨尽春风”的连载佳作《重生后,我成了权臣的对照组》是您闲暇时光的必备之选,谢景渊闲云居 是文里涉及到的灵魂人物,超爽情节主要讲述的是: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彼时的谢景渊,只是个家道中落的穷秀才,空有一身才华和一副清俊皮囊。我们沈家商户出身,有钱无势,父亲看中……
章节预览
我死在建昭三十七年的冬天,死于一杯毒酒。我的夫君,当朝首辅谢景渊,亲手端给我。
他抱着我冰冷的尸身,哭得肝肠寸断,演了一出情深不寿的戏码给天下人看。可我知道,
这杯酒是他默许的。我是他权谋路上最后一块,也是最碍事的垫脚石。用我的死,
换来政敌的彻底倒台和皇帝的全然信任,这笔买卖,他从不觉亏。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
我只有一个念头——若有来生,谢景渊,我愿与你,永不相见。再睁眼,我回到了十六岁。
屋外,媒婆的喜声尖锐刺耳:“恭喜沈老爷,贺喜沈老爷!府上大**与谢家公子的八字,
那是天作之合啊!”1.“这门亲事,我不同意。”我平静的声音,
像一颗石子投入滚沸的油锅,瞬间炸响了整个花厅。父亲猛地一拍桌子,
茶杯震得叮当作响:“沈若渝,你疯了不成!谢家公子少年英才,前途无量,
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你还敢在这里挑三拣四?”母亲在一旁急得直抹眼泪,
拉着我的袖子小声劝:“渝儿,别跟你爹置气。这桩婚事是爹娘为你千挑万选的,
谢公子的人品才学,整个京城都是有口皆碑的。”有口皆碑?我心中冷笑。是啊,上一世,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彼时的谢景渊,只是个家道中落的穷秀才,
空有一身才华和一副清俊皮囊。我们沈家商户出身,有钱无势,父亲看中他的潜力,
不惜血本地资助他,将我嫁给他,只为将来他能成为沈家的靠山。而我,
也被他那句“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誓言迷了心窍,掏心掏肺地为他谋划,
动用娘家所有的人脉和财力,为他铺就一条青云路。他成功了。从一个小小翰林,
一路攀上权力之巅,成为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而我呢?我成了他府中最无趣的摆设。
他身边很快有了善解人意的解语花,有了家世显赫的红颜知己。
而我这个只会谈论柴米油盐和商铺账本的糟糠妻,成了他完美履历上的一点瑕疵。最后,
连我的性命,都成了他权衡利弊后,可以随意舍弃的筹码。“福气?这福气谁爱要谁要。
”我挣开母亲的手,目光直视着盛怒的父亲,“爹,您想投资,女儿不拦着。
但别拿女儿的一辈子当赌注。”“你!”父亲气得脸色涨红。我深吸一口气,
抛出了早就想好的说辞:“女儿前夜梦魇,梦见谢公子将来官运亨通,却妻妾成群,
女儿更是……更是红颜薄命。爹,这桩婚事,不祥啊!”在这个信奉鬼神的年代,
“托梦”之说,最是唬人。果然,父亲的怒气滞住了,脸上浮现出一丝疑虑。
我趁热打铁:“爹若不信,大可去查查城南李侍郎家。他家公子虽顽劣,
但命格里带的却是‘旺妻’。女儿所求不多,一生平安顺遂足矣。
至于谢公子那样的乘龙快婿,咱们家,怕是无福消受。
”我当然知道李侍郎家的公子是个混世魔王,而且不出三年就会因为意外而亡。但我更知道,
父亲的野心,让他不可能真的把我嫁给一个纨绔子弟。我只是需要一个理由,
一个让他暂时搁置与谢家婚事的理由。父亲沉默了。他是个商人,最懂趋利避害。
一个前途未卜的投资,和一个可能带来“不祥”的联姻,孰轻孰重,他掂量得清。见他动摇,
我立刻跪下,泫然欲泣:“女儿自知多言,惹爹爹生气。女儿愿去乡下庄子为母亲诵经祈福,
静思己过。只求爹爹,收回成命。”去乡下庄子,远离京城的旋涡,远离谢景渊。这,
才是我真正的目的。父亲最终还是同意了。他或许是信了我的梦魇之说,
又或许是被我决绝的态度惊到,总之,沈家以我“八字不合,恐有相克”为由,
婉拒了与谢家的婚事。消息传出,京城里一片哗然。所有人都笑话沈家有眼无珠,
放着谢景渊这样的潜力股不要,简直是愚不可及。谢景渊的同窗好友更是当众为他抱不平,
说我沈若渝嫌贫爱富,薄情寡义。我不在乎。别人的口水,淹不死我。但谢景渊的枕边,
却能要了我的命。临行前,母亲偷偷塞给我一个沉甸甸的匣子,
里面是她所有的私房和几张地契。“渝儿,娘知道你是个有主意的孩子。到了乡下,
好好照顾自己,若过得不舒心,就给娘写信,娘去接你回来。”她红着眼眶,满是不舍。
我抱着母亲,感受着这失而复得的温暖,心中酸涩。上一世,我为了谢景渊,
与家里闹得极不愉快,后来沈家被政敌构陷,满门抄斩,我连为他们收尸都做不到。这一世,
我定要护他们周全。“娘,您放心。女儿会过得很好。”我带着两个忠心的丫鬟,
坐着一辆不起眼的马车,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京城。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位于城郊百里外,
母亲陪嫁的一处庄子,名叫“闲云居”。上一世,我从未踏足过这里。只依稀记得,
母亲提过那儿山清水秀,很是安静。安静,正是我现在最需要的。马车摇摇晃晃,
我的心却前所未有的平静。京城的繁华与喧嚣,谢景渊的清冷与算计,
都被我远远地抛在了身后。重生一场,我不想复仇,亦不想再争斗。他要他的青云路,
我要我的独木桥。此生,但愿两不相干。2.马车行了两日,终于抵达了闲云居。
庄子比我想象的还要破败些。几间青瓦房摇摇欲坠,院子里杂草丛生,几乎无处下脚。
只有一个年迈的庄头王伯,带着他老伴守着这偌大的地方。见到我们,
老两口激动得热泪盈眶。丫鬟春桃看着眼前的景象,小脸都皱成了一团:“**,
这……这怎么住人啊?”我却笑了。越是破败,越好。这说明,这里早已被世人遗忘。
一个被遗忘的地方,一个被遗忘的人,正好。我卷起袖子,拿出母亲给的银钱,
开始着手改造我的新家。“王伯,您帮我找些可靠的瓦匠和木工,先把这几间屋子修葺一下,
务必结实。”“春桃,你去镇上采买些米面粮油,还有锅碗瓢盆。”“秋月,你跟我来,
我们把这院子里的草除了。”主仆三人,加上王伯老两口,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我从未做过这些粗活,但心里却充满了干劲。每拔掉一棵草,每擦净一块砖,
都像是在扫除前世的阴霾。前世在首辅府,我锦衣玉食,却活得像个提线木偶,
连笑都得看谢景渊的心情。如今布衣素食,亲力亲为,却感到了久违的踏实和自由。
半个月后,闲云居焕然一新。屋舍修葺一新,窗明几净。院子里的杂草被清理干净,
露出了肥沃的黑土地。我按照记忆中的现代知识,将院子规划成几块,一块种些时令蔬菜,
一块种上我喜欢的花草。我还请人在院子角落搭了个葡萄架,又在屋后开辟了一小片池塘,
养了几尾锦鲤。日子清贫,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我脱下繁复的衣裙,换上简单的布裙,
每日里带着丫鬟侍弄花草,喂鱼浇菜,偶尔去后山采些野果野菜,改善伙食。闲暇时,
便坐在廊下,泡一壶清茶,读几卷闲书。山风拂过,带来阵阵花香,岁月静好,
仿佛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我几乎要忘了京城,忘了那个叫谢景渊的人。直到那天,
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宁静。那天午后,我正在葡萄架下看书,
王伯领着一个青衣少年走了进来。少年身形清瘦,面容俊秀,
眉宇间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郁色和疏离。即使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也难掩其卓然的气质。
是谢景渊。他怎么会找到这里来?我的心猛地一沉,握着书卷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他看到我,
似乎也愣了一下。或许是没想到,传闻中那个“为情所伤,静思己过”的沈家大**,
竟是这般模样。我穿着一身粗布裙,发髻上只簪了根木钗,脸上未施粉黛,
脚边还沾着些许泥土。这与他记忆中那个总是盛装打扮、小心翼翼讨好他的沈若渝,
判若两人。“沈**。”他先开了口,声音清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我放下书,
站起身,朝他福了福身,语气平淡得像在对待一个陌生人:“谢公子,别来无恙。
”没有质问,没有怨怼,甚至没有半分惊讶。我的平静,显然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他沉默片刻,才道:“我听闻沈家退婚,是因为**……身体不适。在下不才,略通医理,
特来探望。”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上一世,他用这副悲天悯人的模样,骗过了多少人,
也包括我。我笑了笑,指了指院子里生机勃勃的菜畦和花圃:“有劳谢公子挂心。不过,
我吃得好,睡得香,身体好得很。”我的言外之意是:我没病,退婚就是不想嫁给你。
谢景渊是何等聪明的人,自然听得懂。他的脸色微不可察地白了一瞬,
那双总是深不见底的眸子里,第一次流露出了些许狼狈。“为何?”他几乎是脱口而出。
“什么为何?”我故作不解。“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他向前一步,目光紧紧地盯着我,
“若渝,你我相识多年,我对你的心意,你应该明白。”心意?我差点笑出声。他的心意,
就是把我当成他平步青云的垫脚石吗?“谢公子说笑了。”我后退一步,
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从前是我年少无知,不懂深浅,多有叨扰。如今想明白了,
你我并非良配,强求无益。谢公子才高八斗,前程似锦,将来必定能觅得佳偶。至于我,
只想在这乡野之间,了此残生。”“了此残生?”谢景渊眉头紧锁,
似乎觉得这四个字从我口中说出,是天大的笑话,“沈若渝,你到底在闹什么脾气?
是因为我前日与王尚书家的千金多说了几句话?我与她并无私情,你……”“谢公子。
”我打断他,语气加重了几分,“我没有闹脾气。我很认真。”我看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道:“谢景渊,我们退婚,与旁人无关。只是因为,我不想嫁给你了。
这个理由,够不够清楚?”空气瞬间凝固。谢景渊的脸上血色尽褪。他大概从未想过,
那个一直追在他身后,将他视若神明的沈若渝,会用这样决绝的语气,对他说出这番话。
这比任何恶毒的咒骂,都更让他难堪。3.谢景渊最终是带着一身的薄怒和不解离开的。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知道,以他的骄傲,被我如此当面拒绝,
短时间内是不会再来纠缠了。春桃端来一碗冰镇绿豆汤,担忧地问:“**,
您就这么把谢公子气走了,万一他将来……报复咱们怎么办?”“他不会。”我笃定地说道。
至少,现在的谢景渊还不会。他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通过秋闱,考取功名。
他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对付一个“无足轻重”的我。至于将来?等他权倾朝野的时候,
我早已是山高水远,他想找也未必找得到了。“不说他了。”我接过绿豆汤,喝了一大口,
清甜的凉意沁入心脾,“咱们的香露和花茶做得怎么样了?”来到闲云居后,
我并没有真的打算“了此残生”。手中有钱,心中不慌。我必须为自己,为母亲,也为沈家,
谋一条后路。我利用自己对花草的了解,以及一些超前的理念,
开始尝试**纯露、精油和各种花草茶。这个时代,女儿家的妆粉香膏种类繁多,
但大多工艺粗糙,气味浓烈。像我这样做出来的纯天然、气味清新的产品,几乎没有。
我将做好的样品托人带给母亲,请她帮忙在京中相熟的贵妇圈里推广。母亲起初不解,
但在看到我附上的详细的计划书和成本利润分析后,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图。她虽是内宅妇人,
却也颇有些经商头脑,当即表示会全力支持。果然,不出一个月,母亲就传信来说,
我做的玫瑰纯露和茉莉香膏在京中贵妇圈里大受欢迎,订单如雪片般飞来。
我立刻扩大了生产规模,雇佣了庄子附近的村民帮忙采摘花草、进行简单的加工,
不仅解决了人手问题,也为村民们提供了一份收入,大家的关系也愈发融洽。我的小作坊,
就这么红红火火地开张了。日子在忙碌和充实中一天天过去。秋天的时候,
我收到了京城来的消息。谢景渊,高中秋闱第一名,解元。一时间,京城震动,谢景渊之名,
无人不晓。当初嘲笑我们沈家有眼无珠的人,如今更是把我们当成了全京城的笑柄。
父亲来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懊悔,隐晦地提出,想让我回京,看看能否与谢家重修旧好。
我只回了八个字:“覆水难收,好自为之。”父亲没有再来信。
或许是我的决绝让他彻底死了心,又或许是我的小作坊赚的钱,
已经足够让他看到另一条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的路。我给家里寄去的银子,
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沈家准备资助谢景渊的数额。金钱,有时候比权势,更能给人带来底气。
转眼三年过去。我的闲云居,已经从一个破败的庄子,变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世外桃源。
我买下了周围大片的山地,种满了各种香草和花卉。春天有桃花和玫瑰,
夏天有茉莉和薰衣草,秋天有桂花和菊花,冬天有腊梅和水仙。一年四季,花开不败,
香气袭人。我的“闲云香坊”也成了大周朝数一数二的胭脂水粉品牌,分店开遍了各大城市。
甚至有西域的商队,不远万里前来求购我的香露和精油。
我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附于家族和夫君的深闺女子,
而是成了别人口中神秘而富有的“沈庄主”。而谢景渊,也如上一世般,扶摇直上。
他中了状元,进了翰林院,凭借着出色的才华和滴水不漏的手腕,在官场上如鱼得水。
短短三年,便从一个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升到了正四品的少詹事。
他娶了吏部侍郎的嫡女为妻,强强联合,仕途越发顺遂。我们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越走越远。我以为,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交集。直到那年夏天,
江南大旱,朝廷派钦差下来巡视灾情。而领头的钦差大臣,正是谢景渊。
4.他的仪仗队路过我们镇子,需要在驿站休整一晚。地方官为了讨好他,
搜罗了本地所有最好的东西送去。其中,就有我们闲云香坊最顶级的“雪肤膏”。据说,
当谢景渊看到那个熟悉的、刻着“闲云”二字的瓷瓶时,当场就变了脸色。
他问地方官:“这闲云香坊的东家,是何人?”地方官自然不知,
只说是位隐居在城外闲云居的沈姓女子。谢景渊沉默了。那一夜,他没有住在驿站,
而是带着两个随从,悄悄地来到了闲云居外。那时我并不知道谢景渊就在外面。
夏夜的风很舒服,我正在院子里教我收养的几个孤儿认字。这几年,
我陆续收养了七八个在灾荒中失去父母的孩童。我教他们读书写字,
也教他们辨识花草、**香露的技艺。闲云居因此多了许多欢声笑语,
也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我抱着最小的女孩丫丫,哼着一首简单的童谣,孩子们围在我身边,
仰着头,看着满天的繁星,一脸的幸福和安宁。月光下,我的侧脸柔和,
眉眼间带着淡淡的笑意。这幅景象,悉数落入了墙外那双深邃的眼眸中。
后来我听当时跟随他的侍卫说,谢大人在墙外站了整整一夜。他看着我教孩子们认字,
看着我给他们讲故事,看着我为他们掖好被角,熄灭灯火。天快亮的时候,他才转身离开。
侍卫说,他从未见过大人那样的表情。不是愤怒,也不是悲伤,而是一种……他形容不出的,
混杂着嫉妒与茫然的情绪。仿佛他穷尽一生去追逐的珍宝,到头来,
还不如别人院子里的一捧萤火。谢景渊没有来见我。他的钦差队伍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
仿佛他从未在镇上停留过。但我知道,他来过。从那天起,
京城里开始源源不断地有东西送到闲云居。起初是些名贵的珠宝首饰,绫罗绸缎。
我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后来又送来各种珍稀的古籍字画,文房四宝。
我挑了几本感兴趣的留下,其余的,都送去了镇上的学堂。再后来,他似乎摸清了我的喜好,
开始送来一些天下难寻的奇花异草的种子。这一次,我收下了。
我将那些种子种在我的花园里,精心培育,看着它们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
但我从未回过一封信,说过一句感谢。我们就这样,维持着一种诡异的默契。他不断地送,
我选择性地收。谁也不点破。春桃她们看不懂,小心翼翼地问我:“**,
谢大人这是……是什么意思?他不是已经娶妻了吗?”“他什么意思,不重要。
”我一边修剪着花枝,一边淡淡地说道,“重要的是,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谢景渊的心思,我比谁都清楚。他这样的人,骨子里是极度自负和有占有欲的。
当初我的“背离”,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失控。他无法接受,那个曾经满心满眼都是他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