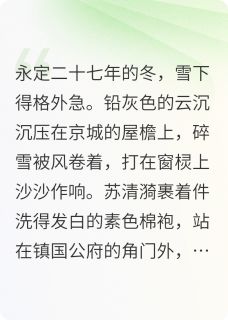《朱墙雪,故人心》是火水冰创作的一部令人过目难忘的古代言情小说。故事中的主角萧玦苏清漪周伯经历了曲折离奇的冒险,同时也面临着成长与责任的考验。小说以其紧凑扣人的情节和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吸引了大量读者。像结了冰:“你怎么来了?”“我来问你,”她攥着衣襟,指甲掐进肉里,才没让自己倒下,……。
章节预览
永定二十七年的冬,雪下得格外急。铅灰色的云沉沉压在京城的屋檐上,碎雪被风卷着,
打在窗棂上沙沙作响。苏清漪裹着件洗得发白的素色棉袍,站在镇国公府的角门外,
指尖冻得通红,连带着露在外面的耳尖也泛着青。门内隐约传来丝竹声,
是《霓裳羽衣曲》的调子,混着暖融融的酒气飘出来,和她身上的寒气格格不入,
像隔着两个世界。“姑娘,这儿真不是你该来的地儿。”守门的老仆姓周,
是府里待了三十年的老人,瞧着她冻得发抖的样子,叹了口气,
从怀里摸出个还热乎的烤红薯,塞到她手里,“快回吧,天这么冷,冻坏了可咋整?
世子他……怕是顾不上这边了。”苏清漪攥着烤红薯,暖意顺着掌心一点点往上爬,
爬到心口,却被那里的冰疙瘩挡着,散不开。
她抬头望向内院那片亮着灯的楼宇——飞檐翘角上积了层薄雪,窗纸上映出人影晃动,
镇国公世子萧玦,此刻或许正拥着新纳的侧妃,在暖阁里饮酒赏雪吧。谁还会记得,
三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雪天,他在京郊别院的桃花树下对她说,“清漪,等我功成名就,
便八抬大轿娶你进门,再不让你受半分寒”。烤红薯的皮被她攥得发软,
甜香混着雪气钻进鼻腔,她却忽然想起那年桃花树下的风,软乎乎的,带着花瓣的香,
比这烤红薯暖多了。一、桃花雪,旧誓言苏清漪认识萧玦时,他还不是镇国公府的世子,
只是个被嫡母苛待、扔在京郊别院养病的落魄公子。那年她十六,随父亲在京郊行医。
父亲苏郎中是个老好人,十里八乡的人有个头疼脑热,随叫随到。
京郊那座别院是镇国公府的旧宅,院里住的大多是府里的老弱,父亲常去给他们瞧病。
那天是替别院的老管家周伯瞧咳嗽,刚走到月亮门,就撞见了在桃树下练剑的萧玦。
他穿件月白长衫,料子是好的,却洗得有些发白,袖口还磨了个小角。那时正是初春,
桃花刚打了花苞,他握着柄铁剑,招式倒是利落,只是咳得厉害,
每练几招就要按住胸口喘半天,脸白得像纸,却仍握着剑不肯放,剑穗上的红绸被风吹得飘,
像抹燃在苍白里的火。“公子这是肺疾犯了。”苏清漪忍不住上前,从药箱里摸出个小瓷瓶,
递过去,“我爹配的润肺丸,含一粒能缓些。再练下去要伤了根基。”萧玦回头看她,
眉眼是真清俊,剑眉斜飞入鬓,只是脸色太淡,衬得那双眼睛格外黑。他咳着笑了笑,
声音有些哑:“多谢姑娘。只是我若不练,将来怎么替母妃报仇。
”那是她第一次听他提“母妃”。后来才知道,他的生母原是镇国公的侧妃,温柔贤淑,
却被嫡母柳氏诬陷与人私通,一杯毒酒赐死了。柳氏怕他长大报仇,处处苛待,
寻了个由头就把他打发到京郊别院,美其名曰“养病”,实则是想让他在这儿自生自灭。
自那以后,苏清漪常去别院。有时是替父亲送药,
有时是带些父亲做的山药糕——她知道萧玦在别院吃得不好,厨房的厨子是柳氏的心腹,
给他端来的饭常是冷的,菜也寡淡。她去了,就坐在桃树下的石凳上,看着他读书、练剑。
他话不多,却心细。她来时,
丫鬟扫净石凳上的落叶;她被别院的恶仆刁难——有次柳氏派来的婆子见她总往萧玦跟前凑,
抬手就要打她,是萧玦冷着脸把人斥退的,他那时虽落魄,身上却有股子天生的贵气,
那婆子竟真的不敢再动;她翻医书时,他会悄悄在她手边放盏温茶,茶温总刚好,
不烫也不凉。有次她来的时候,天上飘了点碎雪,是春雪,落地就化。她缩着脖子搓手,
萧玦忽然解下自己的披风,披在她身上。披风上还带着他的体温,混着淡淡的药香,
她的脸“腾”地红了,想摘下来还他,他却按住她的手:“披着吧,冻病了,
苏郎中该怪我了。”他的指尖温温的,擦过她的手背,像有小虫子爬过,痒得她心尖发颤。
那天的雪落在桃花苞上,亮晶晶的,他站在雪地里看她,眼神软得像化了的雪水。
永定二十四年的春,桃花开得盛。满树粉白,风一吹就簌簌落,像下了场桃花雨。
萧玦在树下给她簪了朵半开的桃花,指尖擦过她的耳尖,温温的:“清漪,我要回京了。
”苏清漪愣了愣,手里的药篮差点掉在地上:“回、回府里?”“嗯。”他点头,眼里有光,
“父亲好像察觉到母妃的事有蹊跷了,让人来接我回去。
镇国公府不能一直被那对母子把持着。”“我等你。”她仰头看他,眼里的光比桃花还亮,
“不管多久,我都等你回来。”他攥着她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清漪,信我。
最多三年,我定禀明圣上,求一道赐婚,风风光光娶你进门。到时候,
我把这院里的桃树都移到咱们的院子里,让你天天能看桃花。”那天的风软,
桃花落在两人发间、肩头,他的誓言像浸了蜜,甜得她心口发颤。她踮起脚尖,
轻轻抱了抱他的腰,他的身子僵了僵,随即用更大的力气回抱住她,下巴抵在她发顶,
轻轻蹭了蹭:“等我。”他回京后,书信从未断过。有时是几张写满相思的诗笺,字迹清俊,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有时是块暖手的玉佩,玉质温润,
上面雕着只小小的鸳鸯;有时只是寥寥数语,说他在府中步步为营,说柳氏处处提防他,
说他夜里总梦到桃花树下的她。她把那些信笺都压在枕下,每晚睡前读一遍,
读着读着就笑了,觉得日子都有了盼头。父亲看她的样子,叹气却也没多问,
只是偶尔会说:“清漪,咱们是小户人家,跟国公府牵扯太深,怕不是好事。
”她那时哪里听得进去,红着眼打断:“爹,他不会负我的。他说过要娶我的。
”可她等啊等,等来的不是赐婚的圣旨,而是他被册封为世子的消息,
还有——他要迎娶丞相千金柳如眉的消息。消息是从京里来的货郎嘴里听说的。
那天货郎在镇上的茶馆歇脚,跟人唠嗑,说京里的新鲜事:“镇国公世子萧玦,你们知道不?
就是以前被扔在京郊的那个,现在可风光了!助圣上查清了当年的旧案,
把他那嫡母柳氏给废了,顺理成章成了世子!丞相大人瞧他前程好,把千金柳如眉许了他,
听说下月就办婚事!”苏清漪正在茶馆角落等着给人送药,手里的药包“啪”地掉在地上,
药材撒了一地——有当归、枸杞,还有她特意给萧玦配的、能养肺的川贝。
邻座的人叹:“听说萧世子以前在京郊养病时,跟个行医的姑娘走得近,
那姑娘还总给他送吃的、送药。现在成了世子,自然要娶名门闺秀,那姑娘……怕是被忘了。
”她没哭,只是默默蹲下身捡药材,手指被粗糙的药根硌得生疼,也没知觉。回到医馆,
她把自己关在屋里,翻出那些信笺,一封封看。看他写“待我归来,定不负你”,
看他写“此生非你不娶”,眼泪才掉下来,大颗大颗的,打湿了纸页,晕开了墨迹,
像把那些誓言都泡得发了软。可她还是存着丝念想。或许是传言错了?或许他有苦衷?
柳如眉是柳氏的侄女,他怎么会娶仇人的侄女?她揣着他送的那块鸳鸯玉佩,连夜往京里赶。
她得当面问问他,问问桃花树下的誓言,还算不算数。二、朱墙内,薄情郎她到镇国公府时,
正赶上府里张灯结彩。红绸子挂了满院,从大门一直缠到内院的暖阁,
下人捧着喜服、红烛来来往往,连空气里都飘着喜庆的香——是沉水香,她在书上见过,
是富贵人家才用得起的。她堵在角门,等了三天。第一天,门房说世子在忙;第二天,
门房把她当成要饭的,赶她走;第三天傍晚,天快黑了,雪又开始下,她冻得快没知觉了,
终于等来了萧玦。他穿着簇新的锦袍,石青色的,上面绣着暗纹的蟒,腰束玉带,
比在京郊时更挺拔,也更陌生。身边跟着的丫鬟捧着个描金的盒子,里面是支凤钗,
红宝石在夕阳下闪着光,亮得刺眼。“萧公子。”她上前一步,声音抖得厉害,像被风吹的。
萧玦回头,看见她时明显愣了愣,眼里闪过丝慌乱,快得像错觉,随即又冷了下来,
像结了冰:“你怎么来了?”“我来问你,”她攥着衣襟,指甲掐进肉里,才没让自己倒下,
“你说过的话,还算数吗?你说要娶我,你说……”他避开她的眼,看向远处挂着的红灯笼,
声音淡得像水:“苏姑娘,此一时彼一时。我如今是镇国公世子,婚事由不得自己。
你回去吧,我会让人送些银两,补偿你。”“补偿?”她笑了,笑得眼泪直流,
泪水落在雪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萧玦,你用银两补偿桃花树下的誓言?
补偿我这三年的等?补偿你在信里写的那些‘相思’?”他皱紧眉,语气添了几分不耐烦,
像被打扰了好事:“苏清漪,别胡搅蛮缠。你我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从前是我糊涂,
耽误了你。”他从袖中摸出个银锭,足有五两重,塞到她手里,“拿着钱,离开京城,
别再出现。”银锭冰凉,硌得她手心疼。她看着他,想从他眼里找到点从前的影子,可没有。
他的眼里只有疏离,还有一丝……厌烦。她忽然想起他信里写的,“清漪,
你的眼睛像含着光的琉璃,我一辈子都看不够”,现在看来,多可笑。他转身就走,
连个回头都没有,红色的灯笼映着他的背影,决绝得像从未认识过她。角门的风吹过来,
卷着院里的沉水香,呛得她喉咙发紧,咳得眼泪更凶了。她没要那银锭,狠狠扔在了地上,
银锭滚进雪堆里,没了踪影。她在京里找了个小杂院住下,就在城边,离镇国公府很远。
杂院破,四面漏风,可她没地方去——她不敢回乡下,怕父亲看到她这副样子心疼。
她靠着替人缝补浆洗糊口,找活的时候,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姑娘手真巧,
就是脸色太差”。她想不通,怎么前一日还在信里说“夜里梦到你”的人,
转头就变得这样薄情。直到他大婚那天。她终究是没忍住,凑了几个铜板,
在街角的酒肆楼上找了个靠窗的位置。街上挤满了人,都来看热闹。她看见他骑着高头大马,
一身大红喜服,胸前戴着红花,比在京郊时意气风发多了。他护着红色的花轿从街上过,
花轿的帘子绣着龙凤呈祥,精致得晃眼。路过酒肆时,花轿里的柳如眉大概是觉得闷,
掀起轿帘一角往外看。那姑娘生得确实好看,眉眼娇俏,皮肤白得像雪,
手腕上戴着串珊瑚珠——那串珊瑚珠,红得像血,她认得。萧玦从前在信里说过,
他母妃有串传下来的珊瑚珠,“等将来娶了你,就把它给你做嫁妆,戴在你手腕上,
定好看”。酒肆里有人喝着酒笑:“听说柳丞相给了镇国公府不少助力,
又是送银子又是拉关系,萧世子才能坐稳世子之位呢!”“可不是嘛!柳氏倒了,
柳丞相还能坐得住?这是想把侄女嫁过去,继续拿捏镇国公府呢!”“也听说了,
他早就把那乡下姑娘忘了,前几日那姑娘来府门口闹,被他赶了呢!”“闹”?
她不过是问了句“誓言还算数吗”,就成了“闹”。她猛地灌了口酒,是最烈的那种,
辣得嗓子像被火烧,眼泪却直流。原来如此。他不是有苦衷,他是为了前程,把她弃了。
她的等待,她的信,她的真心,在他的前程面前,一文不值。那天她喝了很多酒,
走在雪地里,脚下一滑,摔进了结冰的河里。冰水瞬间把她裹住,冷得像刀子割,
可她竟觉得松了口气——或许这样死了,就不用再想了。醒来时躺在杂院的床上,
是隔壁的王大娘救了她。王大娘是个寡妇,靠给人洗衣为生,心善。她发着高烧,
嘴里胡话不断,净是喊着“萧玦”“桃花”。王大娘叹着气,给她敷毛巾,
喂姜汤:“傻姑娘,为了个男人,值得吗?”她不知道值不值得,只知道疼,心口疼,
浑身都疼。病好后,她变了。不再哭,不再等,只是闷头干活。白天替人缝补,
晚上就着油灯学药理——父亲留下的医书她还带在身边,她想,她得活下去,活得好好的,
不能让他看笑话。她要让他知道,没了他,她也能活。可命运偏要跟她开玩笑。
那年冬天京里闹瘟疫,先是从贫民窟开始,很快就蔓延开,杂院附近死了不少人。
官府怕传染,把那片围了起来,没人敢进去。她懂医术,看着街坊们一个个倒下,
孩子哭着喊娘,心里像被揪着,终究是没忍住。她背着药箱,挨家挨户地瞧病。
没日没夜地熬药,给病人喂药、擦身,累得倒头就能睡。她救了不少人,却也染了瘟疫。
刚开始只是咳嗽、发烧,后来就咳血,浑身没力气。弥留之际,她躺在冰冷的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