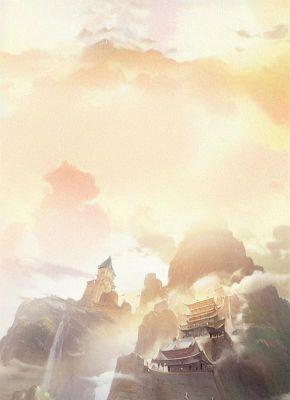《春灯未眠》是一部令人心动的短篇言情小说,由作者潘西来巧妙构思。故事讲述了秦观戴月金晟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踏上了一段无尽的冒险之旅。秦观戴月金晟将面对各种危险和谜题,并结识了一群道义和友谊的伙伴。通过智慧、勇气和毅力,秦观戴月金晟逐渐发现了自己的真正使命,并为之奋斗到底。抽出一封泛黄的信笺。信封上无署名,只有一行小字:“致未来的读者”。他犹豫片刻,拆开。信纸上的字迹清峻有力,正是金晟的手笔……将带领读者探索一个充满惊喜和感动的世界。
章节预览
第一章初遇春灯春三月,北平的风还带着几分料峭,却已不似冬日那般凛冽。
校园里的老槐树抽了新芽,嫩绿如烟,在微光中轻轻摇曳,仿佛一卷未干的水彩,
洇开在灰蓝的天幕下。教学楼前的石阶上,露水未晞,映着晨光,像撒了一地碎银。
钟声自远处悠悠传来,一声,又一声,敲破了清晨的寂静。秦观踏着钟声走进哲学系的大楼。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长衫,袖口微卷,肩头落了一片不知从何处飘来的柳絮。
他手中抱着几本书,最上面那本是但丁的《神曲》,英文译本,书页泛黄,边角微卷,
显是常翻之物。他步履不疾不徐,眉目清朗,眼神却似含着一层薄雾,像是总在思索什么,
又像是什么也不愿深究。这日的讲座由金晟先生主讲,
题为《存在与时间: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教室不大,却座无虚席。学生们或执笔疾书,
或凝神倾听,空气中浮动着一种近乎虔诚的静谧。秦观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
阳光斜斜地切过窗棂,落在他的书页上,将但丁的诗句镀上一层金边。金先生已年近五十,
鬓角微霜,然精神矍铄,声如洪钟。他讲至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时,
忽然停顿,目光扫过全场,缓缓道:“人之为人,不在于思,而在于‘在’——在爱中,
在痛中,在光与影的交界处。你们可曾真正‘在’过一次?”教室里一片沉默。片刻后,
他轻声道:“不如,我们读一段《神曲》吧。《炼狱篇》,第九歌。谁愿试?”无人应答。
窗外风起,吹动了讲台上的稿纸。就在此时,
onlevelwiththegazer’sfeet…”声音如春涧初流,
清澈而微颤,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却又坚定地向前流淌。秦观抬眼望去——是她。
她坐在第三排,侧影清秀,发髻微松,一缕青丝垂在耳后。她低头看着书页,唇齿轻启,
hidbeneaththeskyseemeddim…”秦观的心忽然一动。
他未曾料到,在这间沉闷的哲学教室里,竟会有人以如此温柔而庄重的声音,
读出但丁笔下那穿越炼狱、走向光明的晨光。那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共鸣,
仿佛不只是在读诗,而是在回应某种深埋心底的召唤。他翻开自己的《神曲》,
指尖轻抚那行诗句,随即,
flowers,andsingingasshewent…”他声音不高,
却清晰,带着南方口音的温润,与她的北地清音交织在一起,竟如二重奏般和谐。
她似有所觉,微微侧首,目光穿过人群,落在他身上。四目相对。那一刻,
阳光正巧移过窗棂,落在她的眼里,像一盏初燃的灯。她没有惊,没有羞,只是轻轻一笑,
颔首示意,仿佛他们早已相识多年。秦观也笑了。他合上书,心却未曾平静。讲座结束后,
人群散去,金先生拄着拐杖缓步走出教室。秦观本欲离开,却见那女子仍坐在原位,
低头整理笔记。他犹豫片刻,终是走上前去。“刚才的朗读,很美。”他说。她抬头,
依旧是那抹浅笑:“你也读得很好。很少有人愿意在课堂上接续英文诗。”“是你先开始的。
”他顿了顿,“我不过是应和。”“应和,也是一种默契。”她合上笔记本,
封面上写着两个字:《春灯》。“戴月。”她伸出手,“戴望舒的‘戴’,
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秦观。”他握住她的手,温软而有力,“少游的‘秦观’。
”她笑了:“那你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秦观了。
”他也笑:“可我更喜欢‘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一句。
”两人并肩走出教学楼。春阳正好,照得人通体透明。校园小径上,学生三三两两,
笑语盈盈。他们走得很慢,仿佛时间也愿意为他们驻足。“你常读但丁?”她问。“偶尔。
但真正打动我的,是他笔下那种穿越黑暗、寻找光明的执念。就像……一个人在炼狱中跋涉,
只为再见所爱一面。”“金先生讲‘此在’,我以为,真正的‘在’,或许就是在爱中。
”她望着远处的天空,“你读过金晟先生的信吗?
”秦观一怔:“你指……他与林雪女士的那些旧事?
”她点头:“我曾在图书馆翻到一封他写给友人的信。信中说,林雪病重时,
他每日为她读《神曲》,从《地狱篇》到《天堂篇》,一句一句,
像在为她铺一条通往光明天国的路。可她终究走了。”秦观沉默。“最让我动容的,
是他在追悼会上题的那副挽联。”她轻声念道:“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风忽然静了。秦观只觉心头一震,仿佛有千钧之重压上胸口。那两句诗,他早有所闻,
却从未如此刻般真切地感受到其中的深情与克制。那不是痛哭,不是控诉,
而是一种近乎神性的赞美——将所爱之人,升华为永恒的诗意本身。“你说,
”戴月忽然转头看他,“金先生爱她吗?”“当然。”秦观答得毫不犹豫。“可他从未娶她。
”“他爱的,或许正是她自由的灵魂。若强留,便不是她了。”戴月凝视他片刻,
眼中似有微光闪动:“所以,爱不是占有,而是成全?”秦观望着她,认真道:“我以为,
真正的情感,是守望,而非囚禁。像星光,虽不相触,却共照长夜。”她笑了,
笑容如春水初融:“你倒像金先生的传人。”“我不敢当。我只愿明白,何为‘爱’,
何为‘喜欢’。”“你觉得它们不同?”“喜欢是心动,爱是心定。
喜欢是见她一笑便神魂颠倒,爱是见她落泪仍能**一旁,为她煮一碗热茶。”戴月低头,
指尖轻抚《春灯》的封面:“我写这首诗,便是想写一种‘未眠’的情感——春夜已深,
灯火不熄,人亦不寐。不是不能睡,而是不愿睡。因为有些话,有些人,值得彻夜等候。
”秦观望着她,忽然觉得,这北平的春天,从未如此刻般鲜活。他们走到校门口的旧书店前。
店名曰“未名书屋”,门楣上悬一盏老式煤油灯,虽已改用电灯,却仍保留其形,灯罩微黄,
光晕柔和,仿佛一盏不灭的守望。“进去看看?”戴月问。“好。”店内陈设古旧,
书架高耸至顶,书籍层层叠叠,如时光的积尘。空气中弥漫着纸张与墨香混合的气息,
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檀香。秦观在哲学区翻找,偶然从一本《存在与时间》的夹页中,
抽出一封泛黄的信笺。信封上无署名,只有一行小字:“致未来的读者”。他犹豫片刻,
拆开。信纸上的字迹清峻有力,正是金晟的手笔:“吾生平所学,皆未能解一‘情’字。
林雪之美,如四月天光,不可直视,亦不可久留。我爱之,故退之;爱之,故守之。
若问何为爱?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亦是明知可为而不为的克制。情至深处,
非占有,乃成全。愿后来者,莫困于‘得失’二字,而见‘存在’本身之光华。——金晟,
一九五〇年四月五日”秦观读罢,久久不能言。戴月见他神色有异,轻问:“怎么了?
”他将信递给她。她读完,眼眶微润,却笑了:“原来,我们今日的相遇,
早有人在多年前写下了注脚。”“或许,”秦观轻声道,“每一段情感,
都是前人故事的回声。我们以为是初遇,实则是重逢。”她望着他,阳光从窗缝漏入,
照在她的发梢,如镀金线。“秦观,”她忽然说,“我们还会再见吗?
”“若你愿读《神曲》,”他微笑,“我便愿应和。”她笑了,转身走出书店。
门口风铃轻响,如一声温柔的诺言。秦观立于原地,手中仍握着那封信。灯影摇曳,
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仿佛与金晟的影子,在时光中悄然重叠。春灯未眠,人心亦未眠。
而在这座城市的另一端,梁家旧院的藤椅上,尘埃静静覆盖着一段往事。
那藤椅曾承载过一个哲学家的沉思,也聆听过一位才女的诵读。风穿过院落,
吹动了窗边的旧稿,一页纸上,写着未完的诗句:“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是人间的四月天。”墨迹已干,故事未完。
第二章梁家院落春深了。北平的四月,像一首未完成的诗,风是韵脚,花是意象,而人心,
则是那最微妙的修辞。城南的巷子幽深曲折,青砖灰瓦间,偶有藤蔓攀墙,紫藤初绽,
一串串垂落如梦。巷口有老槐,树影婆娑,筛下点点碎金,落在石板路上,
仿佛时光也放轻了脚步。秦观便是踏着这光影,寻到了梁家旧院。那是一座三进的小四合院,
门楣上悬着一块斑驳的木匾,字迹依稀可辨:“静庐”。门环是铜的,已氧化成青绿色,
叩之,声闷而不响,仿佛岁月早已封存了这里的喧嚣。开门的是个老花匠,姓陈,六十开外,
脸上刻着风霜,却眼神清亮。他见秦观手持金晟先生所赠的信笺,略一打量,
便点头道:“是秦先生吧?金先生早有信来。请进。”院内景致,如一幅褪色的工笔画。
正厅前一方天井,铺着青石板,缝隙间生着细草,随风轻摇。东厢房窗下种着一丛竹,
西墙边则是一架紫藤,花穗低垂,香气清幽。院角有口古井,井台石上覆着青苔,
一只铜吊桶静静悬着,仿佛昨日还有人打水。“这院子,”老陈一边引路,一边低声道,
“三十年前,是梁先生与林**的家。金先生常来,一坐就是半日。”秦观随他穿过天井,
来到后院。此处更为幽静,一株老梅横斜,枝干虬劲,虽已过花期,却仍似存着几分傲骨。
梅树下,放着一张藤椅,椅面磨损,藤条泛白,却擦得极净。“金先生最爱坐这儿。
”老陈轻抚椅背,“每逢林**读《神曲》,他便坐在这儿听。有时闭目,有时凝望她,
从不打断,也不叹息,就那么静静地,像守着一盏将熄未熄的灯。”秦观走近藤椅,
指尖轻触椅面,仿佛能感受到那早已消散的体温。他缓缓坐下,阳光斜照,落在膝上,
暖意融融。“林**……是个怎样的人?”他轻声问。老陈笑了:“她啊,像四月的风,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爱笑,也爱哭。读诗时声音软软的,像春水化冰。可一旦争执起来,
嗓门比谁都高。”“争执?”“是啊。她与梁先生,感情深,脾气也烈。梁先生是建筑师,
心细如发,却固执得紧。林**要改书房的窗,说要‘让光进来’,
梁先生却说‘结构不稳’,两人便吵起来。吵到后来,林**一摔笔,跑了。
梁先生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可手里的图纸,全揉成了团。”秦观听着,
仿佛看见那画面:女子负气而去,男子独坐暗影,窗外春光正好,屋内却似寒冬。
“那后来呢?”“后来?”老陈指向藤椅,“金先生来了。他不劝,也不评,只说:‘峻,
你爱她,是爱她的光,还是怕她的光太亮?’梁先生愣住。金先生又说:‘她要窗,
不是为风景,是为自由。你若真爱她,何不让她透一口气?’”秦观心头一震。
“梁先生想了一夜,次日,亲自改了图纸,加了天窗。林**回来,看见光洒满书房,哭了。
两人抱头痛哭,和好了。”老陈说着,眼中也有微光闪动:“金先生就坐在这儿,看着他们,
一句话不说,只是笑。”秦观仰头,透过藤椅上方的枝叶,望见一片澄澈的蓝天。
他忽然明白,金晟的“守望”,并非冷漠,而是一种更深的参与——他不介入,
却以静默为桥;他不占有,却以理解为舟。“戴**前日也来过。”老陈忽然道。“戴月?
”“是。她在院角那张石桌旁坐了许久,写写停停。走时,留了一页纸在桌上,说若你来,
便交给你。”老陈从怀中取出一张信纸,递了过来。秦观接过,展开——是戴月的字,
清秀如兰:《春灯》春夜不眠,灯花未剪,风推窗,影摇墙,心亦摇。谁在院外轻唤我的名?
声如丝,缠绕不去。我知是你,却不开门。怕一见,便乱了方寸,怕一语,便陷落终生。
爱是光,也是牢笼;喜欢是风,也是火种。我愿做那灯芯,燃在夜里,
不问归程——只为照亮,你路过的那一瞬。秦观读罢,久久无言。他抬头望向院角的石桌,
仿佛还能看见她低头书写的侧影,发丝垂落,笔尖微颤。那首诗,不是情书,
而是一封灵魂的自白——她向往爱,却惧怕被爱所缚;她渴望靠近,却恐惧失去自我。
他忽然懂了她那日的问:“金先生爱她吗?”她真正想问的是:若爱,能否不占有?若喜欢,
能否不沉沦?他将诗稿小心折好,放入怀中。老陈又道:“金先生有次说,
这院子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听过他们的笑声与争吵。他说,真正的感情,不在无争,
而在争后仍愿相守。‘爱不是没有裂痕,’他说,‘而是明知有裂痕,仍愿修补。
’”秦观点头。他想起自己与戴月的初遇,那般温柔,却也那般克制。他们应和诗句,
却未越一步;他们交换心事,却未许诺言。像两片云,在天空相遇,彼此映照,却不相撞。
“我能去书房看看吗?”他问。“可以。但别久留,梁先生后来极少进去,说……太亮了。
”秦观独自走向东厢。门虚掩着,他轻轻推开。书房不大,却极敞亮。一面墙是整排书架,
书籍整齐,多为建筑图册与外文诗集。正中一张大桌,桌上放着绘图工具,
还有一盏老式台灯,灯罩微黄,像凝固的时光。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面新装的天窗。
阳光自上而下倾泻,如一道光瀑,将整个房间洗得通明。书桌、椅子、地板,
皆镀上一层金辉。秦观站在光中,仿佛置身于但丁笔下的天堂——炼狱已过,光明降临。
他走到书架前,随手抽出一本书,是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翻开扉页,
一行钢笔字跃入眼帘:“林:愿你永远有光,哪怕我不在身边。——梁”字迹刚劲,
却有几滴墨迹晕开,似泪痕。秦观轻轻合上书,放回原处。他忽然明白,梁峻的固执,
并非不爱,而是太爱——他怕结构不稳,怕她受伤,怕光太强会灼伤她。可林雪要的,
不是庇护,而是飞翔的自由。而金晟,正是那个看透了这一切的人。他不劝梁峻放手,
只问:“你爱她,是爱她的光,还是怕她的光太亮?”问得多好。爱一个人,
究竟是要她安全,还是让她自由?是要她依附,还是让她飞翔?秦观走出书房,回到后院。
阳光依旧,藤椅静默。他再次坐下,闭目。风过处,
flowers,andsingingasshewent…”是戴月的声音,
还是林雪的?他分不清了。在这院落里,时光仿佛折叠。昨日的爱,今日的思,明日的愁,
皆在春光中交织。金晟的守望,梁峻的挣扎,林雪的追寻,如今又添上他与戴月的踟蹰。爱,
原是一场代代相传的修行。他起身,向老陈道谢。“金先生说,”老陈送他至门口,
“若你明白这院中的事,便也明白‘春灯’为何不眠了。”秦观点头:“灯不眠,因心未静。
心未静,因情未了。”老陈笑了:“你倒是个明白人。”秦观走出小院,
回望那“静庐”二字。紫藤花在风中轻颤,像无数未出口的言语。他知道,
戴月的《春灯》,不只是写给他的诗,
也是写给这院落、这时代、这无数在爱与自由间徘徊的灵魂。春灯未眠,因人间,
永远需要光。第三章鸡棚的温情春意浓时,北平的校园也染上了几分烟火气。
教学楼后的空地上,不知何时搭起了一排低矮的棚子,顶上盖着油毡,四壁是竹篾编的篱笆,
缝隙里透着光,也透着风。棚内传出咯咯的鸡鸣,混着学生们的笑语,
竟成了这象牙塔里最生动的一角。这便是“慰问鸡棚”。秦观与戴月是发起者。
起初不过是一时兴起——某日路过校医院,听闻几位同学因营养不良而病倒,两人商议,
何不养些鸡,每日收蛋,分赠病者?起初只买了五只小鸡,养在纸箱里,置于宿舍窗台。
不料鸡儿长得快,箱中容不下,便在空地搭了棚,渐渐竟有二十多只,羽翼渐丰,
每日咯咯叫着,争食撒在地上的谷粒。秦观常于课余来此。他穿着短褂,袖口挽起,
手中拿着小簸箕,一把把撒着饲料。鸡群围拢,争抢啄食,有的扑翅,有的跳脚,
还有一只芦花鸡,格外机灵,总抢在最前,被学生们戏称为“鸡将军”。戴月来时,
总带着一本书,坐在棚边的小凳上读。她不喂鸡,却爱看它们嬉戏,
看阳光落在它们油亮的羽毛上,像撒了一层金粉。有时她也写诗,笔尖沙沙,与鸡鸣相应,
竟成了一种奇妙的和声。“你倒真像个农夫了。”她笑道。
秦观擦了擦额上的汗:“比在图书馆翻哲学书实在。至少,我知道这鸡今日吃了几顿,
下了几个蛋。”“可你心里,还是在想‘存在’吧?”他笑而不答,
只将簸箕递给她:“试试?”她犹豫片刻,接过簸箕,学着他撒出一把谷粒。鸡群立刻涌上,
她惊得轻呼,脚下一滑,险些跌倒。秦观伸手扶住她肘弯,两人皆是一怔。
阳光正照在她脸上,睫毛微颤,像蝶翼。“谢谢。”她低声道。他松开手,心跳却未平。
鸡棚虽小,却似有魔力,将他们拉得更近。在这里,没有《神曲》的深奥,
没有“爱与喜欢”的哲思,只有最朴素的生计:喂食、清粪、捡蛋。每日清晨,
戴月会来捡拾新下的蛋,用软布包好,送至校医院。她总说:“这蛋是活的,带着鸡的体温,
病人才能好得快。”秦观问:“你怎知鸡有体温?”她笑:“你没摸过?暖的,像人心。
”他于是也学着去摸。果然,那蛋壳微温,仿佛内里藏着一颗小小的心,在轻轻跳动。
一日午后,阴云密布,眼看将雨。秦观急来鸡棚,见戴月已至,正忙着将油毡压紧,
竹篱加固。风起,吹乱了她的发,她伸手去拢,却腾不出手。“我来。”秦观上前,
与她一同拉紧绳索。雨点开始落下,噼啪打在油毡上。两人忙得满头大汗,
忽听“咔嚓”一声,一根竹竿断裂,油毡一角掀开,雨水顿时灌入。“糟了!”戴月惊呼。
秦观不假思索,脱下外衣,扑上去盖住缺口。雨水立刻打湿了他的衬衫,顺着发梢流下。
戴月愣住,随即也脱下自己的外套,与他一同压住油毡。两人并肩蹲在棚下,
头顶是哗哗的雨声,身下是咯咯惊叫的鸡群。“你何必……”她低声说。“它们也是生命。
”他喘着气,“淋病了,谁下蛋?”她望着他湿透的侧脸,忽然笑了:“秦观,
你有时真像个傻子。”“可傻子才最真心。”他也笑。雨渐小,云隙中漏出一线阳光,
照在湿漉漉的鸡棚上,竟映出一道小小的虹。就在此时,老花匠陈伯寻来,
手中捧着一只破碗,碗中盛着几只刚捡的鸡蛋。“金先生旧事,你们可愿听?”他坐下,
轻声道。秦观与戴月点头。“林**病重那年,金先生在她院后养了十几只鸡。每日清晨,
他亲自去捡蛋,说要给她补身子。可林**胃口极差,常吃不下。
金先生便想尽法子:蒸蛋羹,煮蛋花汤,甚至将蛋黄碾碎,混在药里。
”戴月轻问:“他……亲手养?”“是啊。他本是哲学家,手不沾泥,可为了林**,
什么活都肯干。有次他去田里捉虫喂鸡,被蚂蟥咬了脚踝,血流不止,仍不声张。
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只说:‘她若能多吃一口,我少活十年也值。’”秦观默然。
“后来呢?”他问。“后来林**还是走了。”陈伯望着雨后的天空,
“金先生将最后一只鸡放生,说:‘你自由了,她却不能。’”戴月眼眶微湿:“所以,
爱不是宏大的誓言,而是……这些细小的事?”“正是。”陈伯点头,“爱是清晨的一枚蛋,
是雨中的一件外衣,是明知她吃不下,仍愿为她蒸一碗蛋羹的执念。”秦观低头,
看着自己沾满泥土的手。他忽然想起自己与戴月初遇时,
谈的是但丁、是存在、是爱与喜欢的哲学。可如今,他们却为了一群鸡,忙得满身泥水,
只为让病中的同学喝上一碗蛋花汤。这算爱吗?或许不算。可若爱真是“守望而不占有”,
那这每日的喂食、清棚、捡蛋,不正是最朴素的守望?他抬头,
见戴月正凝视着棚内一只母鸡——那鸡刚下完蛋,正咯咯叫着,昂首挺胸,
仿佛在宣告自己的成就。“它真快乐。”戴月轻声道。“因为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秦观说。“人的使命呢?”“或许,就是让别人也快乐。”他望着她,“比如,
让病者好起来,让寒者得暖,让孤独者听见一声鸡鸣。”戴月笑了,笑容如雨后初晴。
自那日后,鸡棚成了他们最常来的地方。他们不再多谈“爱与喜欢”的分别,
却在每日的劳作中,渐渐体会那“细水长流”的真义。有学生不解,笑问:“两位才子佳人,
何苦与鸡为伍?”秦观答:“因鸡不欺人。你喂它,它便下蛋;你护它,它便鸣叫。
人心或难测,鸡心却最真。”戴月则说:“我愿做这鸡棚的守灯人。灯小,光弱,
可若能暖一人心,便不算白燃。”春深时,鸡群开始换羽,旧毛脱落,新羽渐生。
有一只芦花母鸡,尤为特别——它下的蛋,壳上竟有细小的红斑,如血点,又如梅花。
戴月珍而重之,将此蛋存于盒中。“为何留它?”秦观问。“因它不同。”她轻抚蛋壳,
“像一颗不肯熄灭的心。”秦观望着她,忽然明白:她所向往的自由爱情,
或许并非轰轰烈烈的占有,而是如这鸡棚一般——朴素、真实、日复一日的相守。
她不要惊天动地的誓言,只要一个愿为她遮雨的人,一个肯为她捡蛋的人,一个在她病时,
能默默递上一碗蛋羹的人。而他自己呢?他原以为,爱是《神曲》中的光明,
是金晟笔下的“四月天”。可如今,他却在鸡鸣与蛋香中,
触到了爱的另一面——它不在云端,而在泥中;不在诗里,而在日常。爱,原是这般琐碎,
又这般庄严。某日清晨,秦观独自来棚,见戴月已至。她蹲在角落,手中捧着那只芦花鸡,
轻声哼着一支不知名的歌。阳光照在她身上,像为她披了一件金衣。“它老了。”她回头说,
“下蛋少了,别的鸡也欺负它。”“那就让它歇着。”秦观蹲下,“我们养它到老。
”她抬头看他,眼中似有泪光:“秦观,若有一天,我也老了,下不了‘蛋’了,
你还会……守着我吗?”他怔住。这不是哲学问题,而是生命之问。他伸出手,
轻轻覆上她的手背,与她一同捧着那只老鸡。“我会。”他说,
“像金先生守着林**的回忆,像梁峻守着这间书房的光。守着,不是因为你还年轻,
而是因为——你曾照亮过我的春天。”她低头,一滴泪,落在鸡的羽毛上。鸡棚外,
春光正好。风过处,新羽轻扬,如无数细小的翅膀,正悄然生长。
第四章情感的抉择四月将尽,春意渐浓,北平的天却忽明忽暗,如人心般难测。
校园里的紫藤开得正盛,一串串垂落,似梦非梦,风过处,花瓣纷飞,如雨如诉。
图书馆前的长椅上,阳光斑驳,照着一本摊开的诗集,书页微动,仿佛有谁刚离去。
戴月便是从那长椅起身,手中捏着一封信,指尖微颤。信是旧情人所寄,字迹熟悉,
如旧日春风,轻轻拂过心湖,漾起层层涟漪。那人名唤沈之远,曾与她在南方共读诗书,
月下盟誓,后因家事远赴南洋,音信渐稀。她原以为情已如烟散尽,不料今春,
竟得此信——他归国了,愿重续前缘。她站在图书馆的廊下,风穿过回廊,吹起她的发丝,
也吹乱了她的心绪。信纸上的字,一句句浮起:“月:十年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