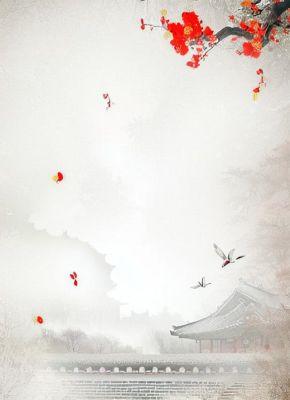《民俗恐怖故事:陪嫁骨簪》这部短篇言情类型的小说很吸引人,是由作者夏勒芬妮写的!主角为林砚秋骨簪李哲小说描述的是:我会不会有危险?”“别急,别急。”王婆婆从竹篮里拿出一张黄符,符纸是用朱砂画的,……
章节预览
林砚秋是被指甲刮擦木板的声音弄醒的。那声音不是连贯的,
而是“咔——咔——”的,像是有人用干枯的指尖,
一下下抠着祠堂门板上的木纹,每一下都精准地卡在心跳的间隙里,听得人牙根发紧。
时值三更,窗外的月光像泡了水的棉絮,沉得透不过气,慢悠悠地压在青瓦上,
给老宅的飞檐镀上一层冷白。她揉着太阳穴坐起身,炕沿的竹席子硌得掌心发疼,
那刮擦声还在断断续续地响,从东厢房隔壁的祠堂飘过来,
混着老樟树叶子“哗啦”的轻响,在空荡的老宅里织成一张阴冷的网。“谁啊?
”她朝着门外喊了一声,声音刚出口就被空气吸走,只撞出细碎的回音,
落在墙角堆着的旧木箱上,惊得一只灰老鼠“嗖”地窜进了缝隙里。刮擦声骤然停了。
林砚秋披上衣裳,赤着脚踩在冰凉的青砖地上。砖缝里还嵌着几十年前的灰尘,沾在脚底板,
凉得像贴了块冰。祖宅是爷爷上个月走后留给她的,在皖南深山里的月亮湾村,
青砖黛瓦的院落里栽着棵三百年的老樟树,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
枝桠上缠着一圈圈褪色的红绸,风一吹就飘得像招魂的幡——据村里老人说,
那是光绪年间用来镇邪的,可红绸的褶皱里,不知藏了多少代人的潮气与恐惧。她这次来,
本是为了整理爷爷的遗物,顺便把这栋闲置多年的老宅挂牌出售。可自打她前天踏进院门,
就总觉得不对劲:夜里总听到樟树下有脚步声,晾晒的衣裳第二天会沾着莫名的泥点,
就连喝水的瓷碗,碗底偶尔会沉着几粒黑色的香灰。祠堂就在东厢房隔壁,常年锁着。
爷爷在世时总说,祠堂里供着月亮湾村的“根”,外人不能随便进。他每次提起祠堂,
声音都会压低,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的补丁,像是怕被什么东西听了去。可刚才那声音,
分明是从祠堂里传出来的,离得那么近,仿佛门板后就站着个人。林砚秋摸到门后的铜锁,
借着月光一看,锁鼻上的铜锈厚得发黑,还沾着几点绿色的霉斑,
锁芯里塞着的旧棉花没有丝毫松动——这锁至少有十年没开过了,绝不可能被撬动。
“难道是老鼠?”她嘀咕着,转身想回房,脚刚抬起来,却猛地顿住。
祠堂窗纸上映着个影子,正斜斜地落在地面上,被月光拉得老长。那影子很高,
瘦得像根枯木,肩线垮着,像是扛不住什么重物。诡异的是,影子的头顶光秃秃的,
没有头发的轮廓,可在脖颈处,却飘着几缕细长的黑丝,随着风轻轻晃,
像是女人垂落的头发,在月光下泛着冷光。林砚秋的心脏猛地一缩,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
她屏住呼吸,脚步放得极轻,一点点挪到窗台下。窗纸破了个小洞,是被虫蛀的,
边缘还挂着几根残破的纤维。她顺着破洞往里看,祠堂里的景象让她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祠堂里点着两盏长明灯,灯油是劣质的菜籽油,昏黄的光线下泛着一层油腻的光晕,
把供桌的影子拉得歪歪扭扭,投在墙上像个张牙舞爪的怪物。供桌上摆着七个牌位,
黑檀木的牌身裂着细缝,上面的字被香火熏得发黑,只能看清“张”“李”几个姓氏。
每个牌位前都放着一碗清水,水面上飘着一层灰,显然很久没人换过了。而那影子的主人,
正背对着她站在供桌前。他穿着件灰布长衫,布料磨得发亮,后颈的头发稀稀疏疏,
露出青灰色的皮肤。他手里拿着个东西,低着头,用一块白布轻轻擦拭,动作慢得诡异,
像是在抚摸什么珍宝。是那支骨簪。林砚秋的瞳孔骤然收缩。那骨簪通体雪白,
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冷幽幽的光,簪头雕着朵莲花,
花瓣的纹路清晰得能看清脉络——她认得这支骨簪,爷爷的遗物里有个紫檀木盒,
盒面刻着“平安”二字,里面就装着这支骨簪,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是爷爷的字迹,
歪歪扭扭地写着:“七月十四,勿让骨簪见月。”今天,正是七月十四。风突然大了些,
祠堂的门“吱呀”响了一声,长明灯的火焰猛地晃了晃,差点熄灭。
那影子突然停住了动作,肩膀微微抬了抬,像是在听什么。林砚秋吓得大气不敢出,
指尖掐进了掌心,疼得发麻。下一秒,那影子猛地转了过来。林砚秋还没看清他的脸,
就见他朝着窗户扑来,动作快得像阵风。窗纸“哗啦”一声被撞破,碎纸渣子飞了满脸,
一股阴冷的风裹着纸钱的灰烬吹了出来,带着一股腐朽的檀香味道,呛得她直咳嗽。
她只觉得脖子一凉,像是有什么冰冷的东西划过皮肤,触感细腻又坚硬,像是骨头。紧接着,
一阵眩晕感袭来,眼前的祠堂、月光、老樟树的影子都开始旋转,最后变成一片漆黑,
她像被抽空了力气,直直地倒了下去。再次醒来时,天已经亮了。
林砚秋躺在祠堂门口的石阶上,石阶上的露水打湿了她的衣裳,凉得刺骨。
她撑着身子坐起来,脖子上一阵刺痛,伸手一摸,
指尖沾到一点血迹——那里有一道浅浅的红痕,细得像头发丝,却疼得钻心,
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刮过。祠堂的门开着,门板歪歪地挂在合页上,
上面多了几道深深的划痕,像是被指甲抠出来的。供桌上的牌位倒了一地,
黑檀木的碎片散在油腻的灯油里,那七个牌位有四个摔成了两半,剩下的三个也裂着大口子。
而那支骨簪,不见了。“姑娘,你没事吧?”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带着几分担忧。
林砚秋抬头一看,是村里的王婆婆,她穿着件蓝布围裙,手里挎着个竹篮,
篮子里装着刚采的草药,还沾着露水和泥土。王婆婆的头发全白了,用一根木簪挽着,
脸上的皱纹里嵌着灰尘,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不少。“王婆婆,
”林砚秋撑着石阶站起来,腿还在发软,“我昨晚在祠堂门口晕过去了,
你……你看到什么人了吗?”王婆婆的脸色“唰”地变了,她放下竹篮,快步走过来,
伸手摸了摸林砚秋的脖子。她的手指很凉,带着草药的苦味,触到那道红痕时,
林砚秋明显感觉到她的手颤了一下。“姑娘,你是不是动祠堂里的东西了?
”王婆婆的声音压得很低,眼睛往祠堂里瞟了一眼,又赶紧移开,
像是怕看到什么不该看的。“我没动,”林砚秋摇摇头,声音有些发颤,
“我看到祠堂里有个影子,他在擦那支骨簪,后来……后来我就晕了,骨簪也不见了。
”“骨簪?”王婆婆的声音抖得更厉害了,她抓着林砚秋的手腕,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是不是簪头雕着莲花的那支?雪白雪白的,摸起来凉得像冰?”林砚秋点点头,
心里“咯噔”一下——王婆婆显然知道这支骨簪的来历。“您知道这支骨簪?
”王婆婆叹了口气,拉着林砚秋坐在石阶上,从竹篮里拿出个水囊,拧开盖子递给她。
水囊是羊皮做的,带着一股膻味,里面的水却很凉。“姑娘,
你爷爷没跟你说过月亮湾村的事吧?这支骨簪,是民国二十三年的时候,
村里张家**的陪嫁,当年可是十里八乡都有名的宝贝。”“张家**?
”林砚秋接过水囊,喝了一口水,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却压不住心里的寒意。“是啊,
”王婆婆望着祠堂里的供桌,眼神变得悠远,像是在看几十年前的景象,
“张家是月亮湾村的大户,家里开着染坊,有钱得很。当年张家**叫阿瑶,
长得跟画里的人似的,还识文断字,多少人上门求亲都没成。
后来她跟邻村的李家少爷定了亲,李家也是书香门第,本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可没等花轿进门,李家少爷就病死了。”王婆婆顿了顿,
声音压得更低了:“按照村里的老规矩,未婚的姑娘要是订了亲,男方死了,
得跟男方结阴婚,把尸体抬到男方家合葬,这样才能保住双方的‘福气’。可阿瑶不愿意啊,
她性子烈,说死也不跟个死人拜堂。”林砚秋皱了皱眉,心里一阵发寒:“那后来呢?
”“后来?”王婆婆的声音带着几分悲凉,“结婚那天晚上,她穿着红嫁衣,
偷偷跑到了祠堂,用这支骨簪抹了脖子。血洒了满供桌,连牌位都染红了。
村里人发现的时候,她已经没气了,手里还攥着这支骨簪,眼睛睁得大大的,
像是有天大的冤屈。”风又吹了起来,老樟树的叶子“哗啦”响,像是有人在哭。
王婆婆伸手把林砚秋的头发往耳后捋了捋,指尖的凉意让林砚秋打了个寒颤。
“后来村里人就把她的牌位供在祠堂里,这支骨簪也跟着一起供着,说是能镇住她的怨气。
可每年七月十四,村里都会出点怪事——要么是有人家的鸡丢了,
要么是晒的衣裳被撕烂,老一辈的人都说,是阿瑶的魂回来了,在找她的骨簪。
”林砚秋摸了摸脖子上的红痕,心里的恐惧越来越深:“那现在骨簪不见了,
我会不会有危险?”“别急,别急。”王婆婆从竹篮里拿出一张黄符,符纸是用朱砂画的,
上面的纹路歪歪扭扭,还带着一股艾草的味道。她把黄符塞进林砚秋的手里,
“你先把这个带在身上,贴身放着,能暂时保平安。今天晚上你别待在老宅里,到我家来住,
我再跟村里的老人们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办法把骨簪找回来。”林砚秋接过黄符,
符纸的温度比手还低,她紧紧攥着,心里稍微安定了些。她跟着王婆婆回了家,
王婆婆的家在村东头,是个小小的院落,院里栽着棵桂花树,树干不粗,却枝繁叶茂,
树下摆着个石桌,石桌上还放着半个没吃完的馒头,上面爬着几只蚂蚁。
王婆婆给她倒了杯茶,茶杯是粗瓷的,边缘有个小缺口。茶水是褐色的,飘着几片草药叶子,
喝起来苦苦的,却能压下喉咙里的腥气。“姑娘,你先坐着歇会儿,
我去问问村西头的李大爷,他年轻时跟着你爷爷一起打理过祠堂,说不定知道些门道。
”林砚秋点点头,坐在石凳上。桂花的香味很浓,却盖不住院子角落里的霉味,她环顾四周,
发现院墙上爬着些牵牛花,花瓣却都是白色的,看起来有些诡异——她记得,
牵牛花很少有白色的。她正想开口问,就听到院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踏踏”的,
是皮鞋踩在泥土路上的声音。抬头一看,是个穿着警服的男人,二十多岁的样子,浓眉大眼,
鼻梁很挺,只是脸色有些苍白,像是没休息好。他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封面已经磨破了,
还夹着一支钢笔。“王婆婆,”男人走进院子,看到林砚秋,愣了一下,脚步顿了顿,
“这位是?”“这是林老栓的孙女,叫林砚秋,”王婆婆赶紧介绍,又对着林砚秋说,
“砚秋,这是县里来的李警官,昨天刚到村里,说是来调查失踪案的。
”李警官朝着林砚秋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伸手递过来:“你好,我叫李哲,
负责月亮湾村周边的治安。”林砚秋握了握他的手,他的手很凉,像是刚摸过冰块,
指尖还有一层薄茧。“你好,我叫林砚秋。”“听说你昨晚在老宅里遇到了怪事?
”李哲坐在石凳上,把笔记本放在石桌上,翻开本子,笔尖悬在纸上,
“王婆婆刚才去李大爷家的时候跟我说了,你能跟我详细说说吗?包括那支骨簪,
还有你看到的影子。”林砚秋深吸了一口气,
把昨晚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从指甲刮擦门板的声音,到窗纸上的影子,
再到脖子上的红痕和失踪的骨簪,连王婆婆讲的张家**的故事也没落下。她说话的时候,
手一直在微微发抖,杯子里的茶水晃出了一圈圈涟漪。李哲听得很认真,眉头越皱越紧,
笔记本上写满了字,字迹工整却带着几分潦草。“你说的这种情况,
这个月已经发生第三次了。”他抬起头,眼神严肃,“前两次失踪的人,
一个是村里的赵二,一个是来写生的大学生,都是在七月十四那天,跟你一样,
在老宅附近遇到了怪事,然后就不见了。”“失踪?”林砚秋心里一紧,
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在地上,“他们……他们找到了吗?”李哲摇摇头,
脸色沉了下来:“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村里的人都说是闹鬼,可我不信这些。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查清楚这件事。对了,你爷爷的遗物里,
除了骨簪和那张写着‘七月十四,勿让骨簪见月’的纸条,还有别的东西吗?
比如日记、照片之类的?”林砚秋想了想,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个紫檀木盒。
盒子的边角有些磨损,上面的“平安”二字被摩挲得发亮。“还有这个,里面除了骨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