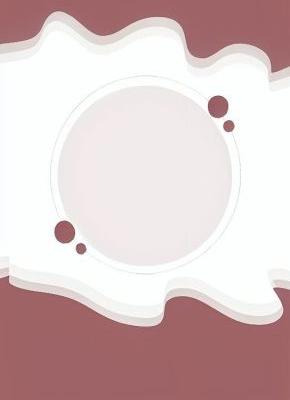这本戏说聊斋:狐鬼人间录写的好微妙微俏。故事情节一环扣一环引人入胜!把主人公李砚胡九娘刻画的淋漓尽致,可谓一本好书!看了意犹未尽!内容精选:胡九娘就轻轻哼了一声,原本紧蹙的眉头舒展了些。「老丈认识清风观的人?」李砚连忙问。……
章节预览
清河县外有座无名山,山不高,却林深雾绕,当地人都说那山里「不干净」。山脚靠着条河,
河边搭了个简陋的渡头,摆渡的是个叫老周的鳏夫,无儿无女,就靠着撑船渡人,勉强糊口。
这年秋末,连着下了半月的冷雨,河水涨了不少,渡口的生意也淡了。
老周裹着件打了补丁的旧棉袄,蹲在渡头的草棚下抽着旱烟,
烟袋锅里的火星在湿冷的空气里明明灭灭。「老人家,渡河。」一个清亮的女声在身后响起,
老周猛一回头,见是个穿月白衫子的姑娘,站在雨丝里,
身影纤弱得像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柳叶。她没打伞,头发却不见湿,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
眼神里映着水光,说不出的灵动。「姑娘,这雨快停了,可夜里山风大,渡河去对岸荒村?」
老周咂咂嘴,「那地方荒了好些年,听说……」「听说有狐有鬼?」姑娘接过话头,
笑意更深了些,「老人家别怕,我不是鬼,也不是狐,就是去寻个故人。」老周挠挠头,
觉得这姑娘说话怪得很,可看她模样,不像歹人,便扛起篙:「上来吧,夜里行船,
多加小心。」船缓缓离岸,破开浑浊的河水,激起一圈圈涟漪。姑娘坐在船尾,
望着岸边渐远的灯火,忽然轻声哼起了调子,调子婉转,带着些说不清的惆怅,
听得老周心里发空。「姑娘,你叫啥?」老周忍不住问。「我姓胡,叫胡九娘。」
「胡九娘……」老周念叨着,忽然想起年轻时听老辈人说过,山里有狐仙,排行第九的那位,
最是聪慧,也最是……多情。他心里一突,偷眼去看,见胡九娘正望着水面,
月光恰好落在她侧脸,肌肤白得像玉,耳朵尖似乎比常人略圆些,却又看不真切。船到对岸,
胡九娘起身,从袖里摸出一小块碎银,递过来:「谢老人家。」老周接过碎银,入手温凉,
不似寻常银子那般冰。他抬头想再说句「夜里小心」,却见岸边空荡荡的,
哪里还有胡九娘的身影?只有一阵风吹过,带来几片落叶,
和一缕淡淡的、像桃花又像青草的香气。「怪哉,怪哉……」老周喃喃自语,撑着船往回走,
只觉得这秋夜的河水,似乎比往日里要暖了些。而此刻,在荒村深处一棵老槐树下,
胡九娘正站在那里,望着不远处一间孤零零的茅屋。茅屋的窗户里透着昏黄的灯光,
隐约能看到一个男子的身影,正伏案读书。她轻轻叹了口气,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有欢喜,有心疼,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忧虑。「李郎,我来寻你了。」她低声说,
声音轻得像叹息,随着风,飘向了远方茅屋里的书生叫李砚,是个落魄的秀才。
他本是清河县人,家境尚可,只因三年前父亲遭人诬陷,家产被抄,父亲病死狱中,
他才避到这荒村,靠着替人抄书、写信,勉强维持生计,却从未放弃过科举的念头。此刻,
李砚正借着一盏油灯的光,研读着《春秋》。窗外风声鹤唳,他却浑然不觉,只是眉头紧锁,
时而拍案,时而叹息。忽然,桌上的油灯「噼啪」一声,灯芯跳了跳,
屋里的温度似乎降了几分。李砚抬头揉了揉眼睛,只觉一阵倦意袭来,便起身想去倒杯热茶。
刚转过身,他却愣住了。只见屋门不知何时开了道缝,一个穿着月白衫子的姑娘,
正站在门后,怯生生地望着他。姑娘生得极美,眉眼如画,肌肤胜雪,只是脸色有些苍白,
眼神里带着几分不安。「你是谁?」李砚心头一紧,这荒村极少有人来,
更何况是这样一位陌生女子,「深夜至此,有何贵干?」姑娘轻轻推开门,走进屋里,
盈盈一拜:「公子莫怕,小女子胡九娘,途经此地,恰逢大雨,想向公子借宿一晚,
不知可否?」她的声音轻柔动听,像山涧的流水。李砚打量着她,见她虽衣衫素雅,
却难掩风姿,不似寻常乡野女子。只是这荒村茅屋简陋,让女子留宿,多有不便。
可看她孤苦无依的模样,又不忍拒绝。「这……」李砚有些为难,「只是在下这里太过简陋,
怕是委屈了姑娘。」「公子肯收留,九娘已感激不尽,怎敢嫌简陋?」胡九娘抬起头,
眼里闪过一丝笑意,「公子若不嫌弃,小女子还会做些针线活,或许能帮公子缝补衣物,
略表谢意。」李砚见她言辞恳切,便点了点头:「既如此,姑娘请自便。只是只有一张床,
我今夜在案前凑合一晚便可。」「公子不必如此。」胡九娘道,「小女子睡外间的柴房便好,
有堆干草,足以安身。」李砚觉得这样更妥当,便取了条旧毯子递给她:「夜里冷,
姑娘盖上吧。」胡九娘接过毯子,指尖不经意间碰到了李砚的手,李砚只觉她的手指冰凉,
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他心里微微一动,却没多想,只当是夜里天凉。胡九娘去了柴房,
李砚重新坐回案前,却再也读不进书了。他总觉得这胡九娘来得蹊跷,可又想不出哪里不对。
她的眼神清澈,举止得体,不像坏人。正思忖间,忽闻柴房传来一声轻咳。李砚起身走过去,
见胡九娘正蜷缩在干草上,脸色比刚才更白了,嘴唇也有些发青。「姑娘可是着凉了?」
胡九娘摇摇头,勉强笑了笑:「无妨,小女子自小体寒,见了风就容易这样。」
李砚看着不忍,转身回屋,把自己盖的薄被取了过来:「这被子厚些,你盖上吧,我年轻,
扛得住。」胡九娘望着他递过来的被子,眼里泛起一层水汽,
轻声道:「公子……为何对我这般好?」「出门在外,谁还没个难处。」
李砚把被子放在她身边,「早些歇息吧。」回到案前,李砚却再也无法平静。
他想起刚才胡九娘的眼神,那里面似乎藏着很多东西,像深不见底的湖水。他不知道,
这个雨夜闯入他茅屋的女子,将会给他的人生带来怎样的波澜。而柴房里的胡九娘,
裹着带着李砚体温的被子,嘴角露出了一抹浅浅的笑意。这笑意里,有温暖,
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她望着茅屋的方向,在心里默念:「李郎,这一世,
我定不会再让你重蹈覆辙。」次日清晨,雨过天晴,阳光透过窗棂洒进茅屋,
照得尘埃在光柱里飞舞。李砚醒来时,发现自己竟趴在案上睡着了。他揉了揉酸痛的脖颈,
转头看向柴房,门虚掩着。走过去一看,柴房里空空如也,只有那床薄被叠得整整齐齐,
放在干草上,旁边还放着他那件打了补丁的旧长衫——原本磨破的袖口,
被人用同色的线细细缝补好,针脚细密,几乎看不出痕迹。「胡姑娘?」李砚喊了一声,
没人应答。他走出茅屋,四下望去,荒村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那名叫胡九娘的姑娘,就像昨夜的一场梦,消失得无影无踪。李砚拿起那件缝补好的长衫,
手指拂过细密的针脚,心里泛起一阵异样的感觉。他确定那不是梦,那女子的身影、声音,
都清晰得仿佛就在眼前。接下来的几日,李砚依旧每日读书,只是时常会走神,
目光总不自觉地飘向柴房,或是望向村口的方向。他心里竟隐隐有些期待,
期待那个月白衫子的身影再次出现。这日傍晚,李砚去村外的小溪打水,回来时,
远远看见自己的茅屋前,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胡九娘。她手里提着一个竹篮,
见李砚回来,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公子。」「胡姑娘?你怎么又来了?」李砚又惊又喜,
快步走上前。「小女子想着公子独自在此,怕是吃不好,便做了些吃食送来。」
胡九娘提起竹篮,里面是一碟酱菜,两个白面馒头,还有一小罐温热的鸡汤,香气扑鼻。
李砚愣住了,他多久没吃过这样像样的饭菜了?眼眶微微发热:「姑娘,这太破费了……」
「公子不必客气。」胡九娘走进屋,熟练地把饭菜摆到桌上,「我住的地方离这不远,
往后若不嫌弃,我常来给公子送些吃的。」李砚看着她忙碌的身影,心里暖烘烘的。
他问:「姑娘住在哪里?我日后也好报答。」胡九娘的动作顿了一下,
随即笑道:「就在山里,说了你也找不到。公子若真想报答,便好好读书,将来金榜题名,
也算不辜负这般苦读。」李砚点点头,心里暗下决心。自那以后,
胡九娘果然时常来探望李砚。有时送些吃食,有时帮他打扫屋子,缝补衣物。
她似乎无所不能,不仅针线活好,还懂诗书,时常能和李砚讨论几句文章,见解独到,
让李砚十分佩服。两人相处的时间久了,渐渐熟络起来。李砚发现,
胡九娘虽然大多时候温柔娴静,偶尔却会露出些孩子气的调皮。比如,她会在李砚读书时,
偷偷把他桌上的砚台换成一块颜色更温润的;会在他背书卡壳时,
假装不经意地提醒一个字;还会在他抱怨夜里冷时,
第二天就让他发现柴房里多了一捆干燥的柴火。李砚越来越觉得离不开胡九娘了。
只是他总觉得,胡九娘身上有很多秘密。她从不说自己的家人,也从不提山里的生活,
而且她似乎很怕狗,有一次村外的野狗追来,她吓得脸色发白,躲在李砚身后,浑身发抖。
还有,她从不在白天走出村子太远,每次日落前,必定要回山里去。这日,
两人坐在老槐树下,看着夕阳染红天际。李砚忍不住问:「九娘,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胡九娘低头玩着衣角,沉默了片刻,抬起头,
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李郎,有些事,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你信我,我绝不会害你。」
李砚看着她清澈的眼睛,心里的疑虑忽然就烟消云散了。他握住她的手,她的手依旧冰凉,
他却想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她:「我信你。不管你是什么人,我都信你。」
胡九娘的眼睛瞬间红了,她反握住李砚的手,低声道:「李郎……」夕阳下,
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将两人的身影笼罩在一起。胡九娘望着李砚的侧脸,
心里却掠过一丝恐惧。她知道,他们这样的日子,恐怕过不了多久了。因为她能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这个荒村,靠近李砚。那是她一直想避开,却终究躲不开的阴影。
那丝阴影来得比胡九娘预想的更快。几日后的一个午后,李砚去镇上送抄好的书稿,
胡九娘在茅屋里替他整理散乱的书卷。忽然,院门外传来几声尖利的狗吠,
紧接着是沉重的脚步声,踏在泥地上,闷响如鼓。胡九娘脸色骤变,指尖捏紧了书卷,
纸页被攥出褶皱。她闪身躲到门后,透过门缝往外看——三个穿着皂衣的汉子,腰挎长刀,
正站在院门口打量着茅屋,为首的是个三角眼,脸上带着疤,眼神阴鸷得像淬了毒的刀子。
「就是这儿?」疤脸汉子扯着嗓子问,声音粗哑。旁边一个瘦高个点头:「头儿,打听了,
那姓李的秀才就躲在这荒村,据说还跟个来历不明的女人来往。」「来历不明?」
疤脸嗤笑一声,「我看是不干不净的东西吧。上头说了,只要跟那姓李的沾边,
不管是人是鬼,都给我带回去问话!」胡九娘心头一沉。是冲着李砚来的,还是冲着她?
她更倾向于后者——这些人身上带着一股熟悉的腥气,
那是常年与阴邪之物打交道才会染上的味道,像是……捉妖人。她悄然后退,
指尖在门框上轻轻一触,一道常人看不见的淡金色光痕隐没在木头里。这是狐族的障眼法,
能暂时挡住凡人的视线,却拦不住真正懂门道的人。「里面有人吗?」瘦高个上前拍门,
「李秀才!出来!」没人应答。疤脸不耐烦了,抬脚就踹,「哐当」一声,
简陋的木门应声而倒。三个汉子涌了进去,屋里空荡荡的,只有一桌一椅一榻,书卷散落,
却不见半个人影。「人呢?」瘦高个挠头。疤脸环顾四周,鼻子嗅了嗅,
眉头皱得更紧:「有妖气,很淡,但刚离开不久。搜!」三人在屋里翻箱倒柜,
刀鞘磕碰着桌腿,发出刺耳的声响。胡九娘就躲在房梁上,屏息凝神,指甲悄然变长,
泛着冷光。她能轻易解决这三个人,但那样会暴露行踪,引来更多麻烦,反而会害了李砚。
就在这时,院外传来李砚的声音:「你们是谁?为何闯我住处?」
胡九娘心一揪——他回来了!李砚刚进院门,
就看见倒在地上的木门和屋里翻得乱七八糟的景象,脸色瞬间涨红。疤脸转身走出屋,
上下打量着他,三角眼眯成一条缝:「你就是李砚?」「正是。」李砚强压怒火,
「诸位是官差?可有公文?为何私闯民宅?」「公文?」疤脸冷笑一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
扔在李砚面前,「奉县太爷手谕,带你回去问话!你爹当年的案子,还没了结呢!」
李砚捡起纸,手指颤抖。三年了,他以为只要躲得远远的,就能避开那些污秽,可该来的,
终究还是来了。「我爹是清白的!」他抬头,眼里燃着怒火。「清白?」疤脸上前一步,
伸手就要抓他,「到了大堂上,看你还敢不敢嘴硬!」就在他的手快要碰到李砚时,
一道白影从房梁上跃下,挡在李砚身前。是胡九娘。「你们要抓他,先过我这关。」
她的声音冷得像冰,眼神里没了往日的温柔,只剩下凛冽的锋芒。疤脸看到她,
眼睛一亮:「果然有个妖女!正好,一并拿下!」他从腰间抽出一张黄色的符纸,
往胡九娘身上拍去,「敕!」符纸靠近胡九娘三尺之地,忽然「轰」的一声燃了起来,
化作一缕青烟。疤脸脸色大变:「你不是普通狐妖!」胡九娘没说话,只是抬手,
指尖弹出几道白光。那三个汉子只觉得一阵风刮过,随即浑身酸软,长刀「哐当」落地,
竟连站都站不稳了。「李郎,走!」胡九娘拉住李砚的手,转身就往村外跑。李砚被她拽着,
脑子里一片混乱。妖女?狐妖?原来……她真的不是人。可他看着她的侧脸,
感受着她冰凉却有力的手指,心里没有恐惧,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她走。两人一路狂奔,
身后传来疤脸气急败坏的叫喊:「妖女!别跑!我乃清风观弟子,定要收了你!」
风声在耳边呼啸,胡九娘的白色裙摆在风中翻飞,像一只受惊的蝶。
李砚忽然想起她曾说过:「这一世,我定不会再让你重蹈覆辙。」原来,
她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原来,她一直都在护着他。跑出荒村,
胡九娘带着李砚钻进了深山。山路崎岖,荆棘丛生,李砚平日里只知读书,
哪里走过这样的路,没一会儿就气喘吁吁,脚踝也被划伤了。「我……我跑不动了。」
他扶住一棵老树,弯腰喘气。胡九娘停下脚步,回头看他,眼里满是歉意:「对不起,李郎,
连累你了。」她蹲下身,轻轻卷起他的裤脚,看着那道渗血的伤口,眉头紧锁。「不怪你。」
李砚喘着气,「是我自己没用……」「别动。」胡九娘从头上拔下一支银簪,
簪头刻着朵小小的桃花。她用簪尖在自己指尖轻轻一划,挤出一滴殷红的血珠,
滴在李砚的伤口上。奇异的事发生了。那血珠落在伤口处,竟像活物般渗了进去,
原本**辣的疼痛瞬间消失,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
李砚瞪大了眼睛:「这……」「狐族心头血,能治凡伤。」胡九娘把银簪插回发间,站起身,
「我们得找个地方躲起来,清风观的人鼻子灵得很,很快就会追上来。」她拉着李砚,
拐进一条更隐蔽的小路。走了约莫一个时辰,眼前出现一片茂密的竹林,竹林深处,
竟有一座破败的古墓,墓门半掩着,上面爬满了藤蔓。「进去躲躲。」胡九娘推开墓门,
一股尘封已久的土腥味扑面而来。墓里很暗,只有几缕阳光从顶部的缝隙照进来,
勉强能看清轮廓。墓室不大,中央放着一口石棺,棺盖已经裂开,
旁边散落着些腐朽的木片和陶俑。「这里……安全吗?」李砚有些不安,他虽是读书人,
却也怕这些阴曹地府般的地方。「暂时安全。」胡九娘点亮了随身携带的火折子,火光摇曳,
映得她的脸忽明忽暗,「这是座空墓,几十年前就被盗墓贼光顾过,阳气散得差不多了,
他们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这里。」李砚点点头,在一块相对干净的石头上坐下。
火光照亮了他的脸,也照亮了他眼底的疑惑。他看着胡九娘,犹豫了很久,
终于开口:「九娘,你……真的是狐妖?」胡九娘握着火折子的手顿了一下,随即转过身,
看着他,眼神里带着一丝忐忑:「是。我是青丘狐族,排行第九,所以叫胡九娘。」
李砚沉默了。他想起这几个月的相处,想起她夜里的清冷,想起她怕狗的样子,
想起她缝补的衣衫……原来那些看似奇怪的地方,都是因为她不是人。「你……」
李砚张了张嘴,想问什么,却又不知从何问起。胡九娘却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
轻声道:「你想问,我为何要接近你?为何要护着你?」李砚点点头。胡九娘叹了口气,
走到石棺旁,指尖拂过棺盖上模糊的刻纹,声音低沉下来:「因为……上辈子,我欠你的。」
「上辈子?」「嗯。」胡九娘的目光飘向远方,仿佛看到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上辈子,
你也是个秀才,叫李砚。那时我刚修成人形,不懂人间规矩,在山里被猎人设的陷阱困住,
是你救了我,把我带回书院,偷偷养着。你教我读书写字,告诉我人间的道理……」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暖意:「那时你说,等你金榜题名,就娶我为妻。可后来,
你进京赶考,却被奸人所害,说你勾结妖邪,革去功名,打入天牢,最后……死在了牢里。」
李砚的心猛地一揪,像是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隐隐作痛。他明明没有上辈子的记忆,
却莫名地觉得难过。「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胡九娘的声音哽咽了,
「我没能护住你。所以这一世,我提前找到你,只想护着你,不让你再遭那些罪。」原来,
她说的「重蹈覆辙」,是这个意思。原来,她对他的好,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跨越了生死的执念。李砚站起身,走到胡九娘面前,轻轻握住她冰凉的手:「九娘,
不管你是人是妖,不管上辈子发生过什么,这辈子,你护着我,我也会护着你。」
胡九娘抬起头,眼里蓄满了泪水,看到李砚坚定的眼神,她忽然笑了,泪水滴落在手背上,
温热的。就在这时,墓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一个尖利的声音:「妖女!
我看你往哪躲!」是清风观的疤脸!他竟然追来了!胡九娘脸色一变,将李砚护在身后,
眼神瞬间变得凌厉:「看来,是躲不过了。」她从袖中抽出一把小巧的弯刀,刀身泛着银光,
「李郎,等下我缠住他们,你趁机往东边跑,那里有片迷雾林,他们进不去。」「我不跑!」
李砚握紧她的手,「要走一起走!」「听话!」胡九娘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你留在这里,
只会让我分心!」墓门「砰」的一声被踹开,疤脸带着两个师弟冲了进来,
手里都拿着符纸和桃木剑,脸上带着狞笑:「妖女,这次看你还有什么本事!」
胡九娘将李砚推开,举起弯刀,迎了上去:「想要伤他,先问问我的刀!」银光闪过,
符纸燃烧的爆炸声在墓室里响起,一场人与妖的厮杀,在这座尘封的古墓里,骤然展开。
李砚看着胡九娘娇小的身影在三个汉子中间穿梭,心里又急又痛,却只能紧紧攥着拳头,
无能为力。他第一次如此痛恨自己的无能,痛恨自己只能眼睁睁看着她为自己拼命。
墓室里的打斗愈发激烈。胡九娘的弯刀如银蛇游走,每一次挥出都带着凛冽的风声,
逼得三个道士连连后退。但那疤脸显然有些道行,手中桃木剑上缠着黄符,符纸遇风自燃,
化作一道道火光射向胡九娘,嘴里还念念有词:「天地无极,乾坤借法,妖物现形!」
胡九娘身法灵动,避开大部分火光,却还是被一道火星燎到了衣袖,「嗤」的一声,
月白衫子顿时焦了一块。她闷哼一声,气息有些紊乱——在这古墓之中,阴气虽重,
却不利于狐族灵力流转,久战之下,她已渐感吃力。「九娘!」李砚看得心急如焚,
忽然瞥见墙角堆着些枯枝,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抱起枯枝就往疤脸身后扔去。
疤脸正全神贯注对付胡九娘,冷不防被枯枝砸中后背,顿时怒火中烧,
回头瞪向李砚:「找死!」他反手一掌拍向李砚,掌风带着一股腥气,显然练过些阴毒功夫。
胡九娘脸色剧变,想也没想就扑过去挡在李砚身前。那掌结结实实打在她背上,她闷哼一声,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九娘!」李砚扶住她,声音都在发抖。
「妖女受创,正是时候!」疤脸见状大喜,举剑就刺,「师弟,结阵!」
另两个道士立刻分站两侧,手中符纸同时燃起,三道黄光交织成一个网,朝着胡九娘罩来。
这阵法专克精怪,一旦被罩住,灵力便会被锁,只能束手就擒。胡九娘看着越来越近的光网,
眼中闪过一丝绝望。她转头看向李砚,眼神里满是不舍:「李郎,忘了我吧……」就在这时,
李砚胸前忽然闪过一道微光。那是他一直贴身戴着的玉佩,是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
玉质温润,上面刻着个模糊的「清」字。此刻,玉佩竟自行发烫,
一道柔和的白光从玉佩中散发出来,恰好撞上那光网。「滋啦——」光网像是被泼了冷水,
瞬间消散,三个道士都被震得后退几步,
疤脸更是惊疑不定地盯着李砚胸前的玉佩:「那是什么东西?」胡九娘也愣住了,
她能感觉到,那白光里蕴含着一股纯净的浩然之气,正是妖邪之物的克星,
却又带着一种温和的庇护之力,并未伤及她。「走!」胡九娘抓住机会,
拉起李砚就往墓后跑。墓后有个被藤蔓遮住的暗门,是她刚才探查时发现的。两人冲出暗门,
身后传来疤脸的怒吼:「别让他们跑了!」胡九娘带着李砚一路狂奔,
朝着东边的迷雾林跑去。她背上的伤让她每一步都痛彻心扉,鲜血染红了月白的衣衫,
在身后拖出一道触目的红痕。「我来背你!」李砚停下脚步,蹲下身子。「来不及了……」
胡九娘摇摇头,声音虚弱,「快到了……」说话间,前方出现一片白茫茫的雾气,
雾气浓得化不开,像是一道天然的屏障。这就是迷雾林,传说进去的人都会迷失方向,
再也走不出来。胡九娘拉着李砚冲进迷雾,刚踏入雾中,
身后的脚步声和怒吼声就骤然消失了,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墙隔开。
雾气里弥漫着潮湿的草木气息,能见度不足三尺,四周静得只能听到两人的呼吸声。
「这里……真的安全吗?」李砚握紧胡九娘的手,生怕走散。「嗯,」胡九娘喘着气,
脸色依旧苍白,「这雾是天然形成的,带着些混沌之气,寻常道士进不来……」话没说完,
她身子一软,就往地上倒去。「九娘!」李砚连忙扶住她,发现她已经晕了过去,
后背的伤口还在渗血。他心急如焚,抱着她在雾里摸索,想找个能歇脚的地方。
不知走了多久,前方忽然出现一点微光。走近了才发现,是一间小小的木屋,
就藏在浓雾深处,屋前还种着几株开得正艳的红梅,在白茫茫的雾气中格外显眼。
李砚抱着胡九娘走到木屋前,轻轻敲门:「请问有人吗?」门「吱呀」一声开了,
一个穿着青布长衫的老者站在门内,须发皆白,眼神却清亮得很,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眼,
淡淡道:「进来吧。」李砚连忙道谢,抱着胡九娘走进屋。屋里陈设简单,一张木桌,
几把椅子,墙角燃着个炭盆,暖意融融。老者指了指里屋的床:「把她放那里吧。」
李砚小心翼翼地将胡九娘放在床上,回头见老者正拿着个药箱走过来,不由得问:「老丈,
您是大夫?」老者没回答,掀开胡九娘后背的衣衫,看了看那掌印,
眉头微蹙:「清风观的阴煞掌,下手倒是狠。」他从药箱里取出几味草药,
又拿出一个小瓷瓶,倒出些黑色的药膏,小心翼翼地涂在伤口上。药膏刚涂上,
胡九娘就轻轻哼了一声,原本紧蹙的眉头舒展了些。「老丈认识清风观的人?」李砚连忙问。
老者站起身,走到炭盆边烤了烤手,才缓缓道:「何止认识。那清风观的观主王道陵,
早年跟我学过几天医术,后来心术不正,迷上了旁门左道,才被我逐出门墙。」
李砚吃了一惊:「原来如此。那不知老丈如何称呼?」「老夫姓陈,」老者淡淡道,
「你叫我陈老丈便是。倒是你,身上带着『清心玉』,却被阴煞掌所伤的妖狐护着,
倒是有趣。」李砚低头看了看胸前的玉佩:「老丈认识这玉佩?」「怎么不认识,」
陈老丈笑了笑,「这玉佩是当年我送给你父亲的。他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可惜啊……」
他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李砚浑身一震:「老丈认识我爹?」
陈老丈点点头:「你爹李修远,当年在清河县做知县时,我曾在他手下做过幕僚。
后来他遭人诬陷,我也被牵连,只能躲到这迷雾林里避世。」原来如此!李砚又惊又喜,
连忙跪下:「老丈!求您告诉我,当年我爹究竟是被谁诬陷的?」陈老丈扶起他,
眼神变得凝重:「起来说。当年诬陷你爹的,明面上是县里的主簿张谦,可他背后,
站着的是知府王启年。而这王启年,与王道陵交情匪浅,
据说两人私下里做了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李砚听得心头火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