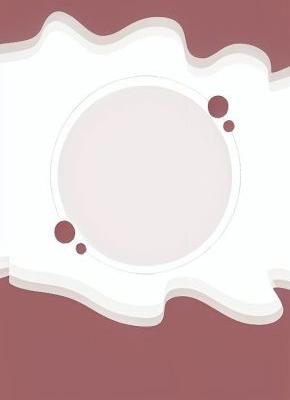《不渡春深》是一部充满爱情与冒险的短篇言情小说,由檀绒精心构思而成。故事中,沈贺舟崔宛旖谢楹经历了一段艰辛的旅程,在途中遇到了[标签:主角的伴侣],二人共同面对着来自内心和外界的考验。他们通过勇敢、坚持和信任,最终战胜了困难,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瓷白的面容晕开一片醉意的酡红。他半睁着一双朦胧的眸,含糊不清地呼唤着另一个人的名,……将唤起读者心中对爱情和勇气的向往。
章节预览
他们都夸我是京城最贤良的王妃。贤良到亲自为他失而复得的白月光筹备婚事。
他说:“阿颜,如今宛旖只有我了,离开我,她怎么活呢?”直到那日荒郊,山匪围困,
刀光刺目。我看着他夺过缰绳,护着怀里的人策马远去,荒草没过我绝望的眼。
是那个记忆中的少年郎将我寻回,一路护送至他面前。县衙灯火通明,他扶着他的白月光,
望向我的眼神却满是责备:“你一个妇道人家,怎能让一个陌生男人触碰你。
”岏都的风很冷,我看着他护住另一个女子的姿态,忽然感到一种彻骨的冰寒。原来,
他不是不会爱人,只是不会爱我。01.崔宛旖回京的车马安抵京那日,
我那成婚五年之久的夫君早早就坐在妆台前。他捧着从前嗤之以鼻的脂粉手忙脚乱地涂抹,
如初开情窦的毛头小子般,是从前未见过的模样。他光是衣裳都换了几身。在耳边絮絮叨叨,
说宛旖最爱美了,要见她自然也该以最好的状态相见。我看着他折腾,
心里有些说不出的酸涩。就在半月前府中收到一封信,上头只有一行:贺舟亲启。
起初沈贺舟并不在意,撑着下颌鼓弄着他那些新觅得的宝贝,便说任我自行处置,
摆手时甚至头都没抬。直至从我口中捕捉到关键内容,
一向以冷静自持的沈贺舟竟在那一刻乱了分寸。我分明看见他眼底的猩红,抖着手,
颤声叫我把信给他。到那一刻,我方知晓,原来我的夫君心里有一位放不下的白月光,
就此般轻而易举的拨动他心弦。他在镜前整衣敛容,一番捯饬,
最后方勉强定了穿前几日赶制好送到府上那身玄色锦袍。倒不是旁的,只是实在是没时间了。
近日中时一两漆黑车驾准时在王府朱门前停稳。马夫方摆好马杌,沈贺舟就迫不及待迎上前,
搀她下车。我立在廊下越过重重人影望见那张玉白明艳的脸,一瞬竟有些恍惚。
原来人真的能相像到这般啊……不同的是,崔宛旖的眉宇更多的是几分倔强。
甚至到此时我方如梦初醒,从前沈贺舟不准许我哭,也是因为她。他们彼此相拥,
一如久别的情人重逢缱绻亲昵。沈贺舟抬手抚她眼睫,眼底是从未给过我分毫的温柔,
眼眸罕见的泛着泪,转头吩管事去安置,为她鞍前马后。我远远望着,
心底却是无休止的凄楚。终于沈贺舟携女子从我跟前经过,那一瞬的驻足,
崔宛旖注意到了我。“她是?”“她是阿颜,是……我的王妃。
”“可贺舟从前不是说非我不娶么?”他轻抚着女子鬓发,眼底皆是爱意,
及那失而复得难掩的欢欣与雀跃:“她一个乡野村妇,哪能与你相比?
”02.当夜沈贺舟在府中设宴,宴请朝臣好友,亦不知到底是为崔宛旖接风,
还是借此贺他失而复得。夜里她是由侍从搀回房的,烂泥一般摊在榻上,
瓷白的面容晕开一片醉意的酡红。他半睁着一双朦胧的眸,含糊不清地呼唤着另一个人的名,
紧紧攥着的却是我的手。“宛旖……宛旖……”我坐在榻边,喃喃开口。“既然那么喜欢她,
当初为何不娶她?”“若非那次争闹,我们便不会错失这些年的时光……可今日我很高兴,
你终于又回到我身边了……”我垂眸望着那只桎梏在腕间的手,听着他那些吐露的酒后真言,
咽喉却像被甚堵住了,丝丝酸涩泛至心头,唇齿翕动着万分艰难才问出一句:“那颜令仪呢?
”“阿颜……”在念及我的名字时,那双迷蒙的眸恍惚有过片刻些微的清明,
可到底稍纵即逝的短暂,许久的静默后,他阖上了眼,“阿颜,是我的王妃,
她……也很好……”与沈贺舟的初见,也是此般融融秋月。他自河畔策马而过,
恰顺手救下落水陷入昏厥的我。我仍记得,那日在阳辉下他展颜的笑意炫目得恍如神明。
到他离开岏都那一日,我方知晓沈贺舟的门第与我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所差的天壤之别,
是我这等平民人家几辈子都不敢痴心妄想的。他离开了两月有余,却忽在一日去而复返。
杨柳树下,他紧紧拥着我落泪,那些深情款款,说他离不开我要带我回汴京。
那时的我以为是上天所眷,让我心仪之人也同样钟情于我。只是……成婚时的头两年,
他时不时就将自己关在书内,如今日这般酩汀大醉一场。我以为他是因朝堂之事劳心,
心疼他操劳,甚至要借酒买醉,早早煮好醒酒汤。
在他醉酒后总那般小心翼翼地跪坐在他身侧,用沾湿的绢布为他盥洗。
他总是偏过头避开我抬起试图为他拭泪的绢帕。当我端来醒酒的茶汤他不耐地挥开,
盛着热汤的瓷碗落地尽碎,而我也遭他推得扑倒在地,手掌按在了碎裂的瓷片上。
碎瓷扎进掌心软肉,而我却不觉疼痛,那些对他的心疼反而越渗越深。可我总该是会委屈的,
见我垂泪又作出怜惜之状,温热的掌逐点抚过我的眉睫。“对不起,我不该凶你。
”他哆嗦着俯身与我额头相抵,重复着:“不要离开我。”滚热的呼吸缠绕着我眼眉,
当粗粝的指腹碾过我眼角的泪时,却加重几分力道,说:“不许哭,阿颜我说过的,
你忘了么?”那时我呆滞地望着他撤回的掌,头一次发觉他种种行为偏偏如此割裂,
叫我分不清虚实。我忽的想起席间他谈及从前过往,眼底皆是欢欣的模样。原来,
不过那都是因我不是崔宛旖罢了。03.崔宛旖才刚死了丈夫,
转头就上了淮阳王府的车马总归还是不好看的。沈贺舟亦然深知这一点,
是以此前就曾商讨决定将崔宛旖认作义妹,至于该如何操办尚未来得及定下,
我还在思索此事,房里的丫头就来禀珍宝坊的伙计送首饰来了。那是一套凤冠头面,
瞧做工与样式,断然是下了苦心精心去安排的。我正为此疑惑,
门扇开合的“吱呀”声骤然打断了我的思绪。沈贺舟披着暮色步入屋室,
木质的门扇再“哐当”的于他身后阖紧,只余下我们与一室的静谧。
而是我最先启了口:“晌午时珍宝坊的伙计送来一套头面,瞧样式该是新嫁娘用的,
莫不是搞错了?”“没搞错。”他惯常地褪下外袍扔到我怀里,一面往里屋走,一面道,
“我已与父皇请旨,娶宛旖为妻。”组合起来字眼几乎是逐字砸进我耳里的,
顷刻化作尖锐的嗡鸣在耳边回响。心一点点的往下沉,却还抱着最后一丝可笑的妄想。
然后我听见了他清晰而缓慢地声音,每一个字都似淬了毒的针,扎进耳膜刺入心脏。
“宛旖过得不好,如今不易从夫家逃离,总得有个依傍。”他沉沉叹息,
不觉间便已辗转至桌前,端起我在他进门起就斟好的热茶一饮而尽。“若不是我,
她也不会赌气嫁与旁人,这是我欠她的。”“你……说什么?”我怔怔地望着他,
看着这个我曾一见倾心,甘愿抛却所有的男人。我一步步往后趔趄,
直至靠在插屏处方堪堪稳住步子,声音轻得像一缕青烟,
带着自己都无法控制的颤抖:“那我呢?王爷是想与我和离么?”“是平妻,
宛旖与你平起平坐,唤你一声姐姐,也委屈不得你。”“若是觉心里有愧,
王爷可以认作义妹。”在话出口的一瞬他蓦地变了脸色,粗粝的掌扼住我的下颌,
迫使我昂首与他视线相汇:“颜令仪,是本王平日对你太好,令你娇纵了是么?
连你都敢指点起本王了?你若不愿那便和离。”良久他终于松开钳制,
任我如枯叶般脱离坠地。他立在跟前,居高临下地俯身,垂眸睥睨。“你也该清楚,
你的荣尊和锦衣玉食都是谁给的,没有本王,你什么都不是。
”我睖睁地望着他依旧俊朗的眉眼,此刻却觉着无比陌生。
不知他可否记得在崔宛旖回京前的某一夜,他曾拥着我保证对她别无心思了呢?
那我的情意算什么?往日那些海誓山盟又算什么呢?那些因他一句“弱水三千,
只取一瓢”而深信不疑的数个日语,又算什么呢?我那般欢喜他。
私以为至少能在他心底有些分量,哪怕只有一点。可都在崔宛旖回到汴京时,化作了乌有。
沈贺舟与崔宛旖的婚事不日便开始筹备,制好的喜袍送至王府时,
我正心不在焉地翻看着礼单,连着橘春在身侧念叨些甚都无心去听。再一次绕过外廊拐角时,
端着瓶盏错身而过的女孩们交谈声不偏不倚落到了我耳里。“岏都那可是水患啊,
听说如今殿下也在为此发愁呢。”“啊……怪不得殿下回府时脸色都不大好。
”瞬间将我从怅然中拉出来。不等我开口,橘春就先猜出了我内心所想,大步走上前。
“你们方才所说的,哪里水患?”04.从前沈贺舟不准许我擅自进入书房。
是以我与橘春甫一踏上外廊时,一如所料的,就遭两柄长剑死死拦了去路,
眼前是值守侍卫冷肃的脸。“殿下外出了,不若王妃先回去等候,等到殿下回府,
属下再命人禀与王妃。”这次我选择了充耳不闻,过兀自推开书房的门。侍卫还要拦,
但橘春抢先展开双臂横在了门前,两人面面相看却也不敢真动手。
炉中香烬尚燃确实是才离开不久的不错。在书案一通寻找无果,
正当要放弃时无意摸着书橱处突起的纹路,轻轻一按随着暗格弹出的还有里头一封封的信笺。
除却他与崔宛旖来往的书信,还有部分……从岏都寄来的,又或是汴京送往家乡的信笺。
……直到入夜他方披着夜色回来。当外廊响起说话声时,我搭在膝上的手不住地紧了紧。
沈贺舟进屋,不过抬眼轻轻瞟我一眼,就兀自宽衣,“大晚上不去歇息坐在这演木雕么?
”外袍随手搭在衣架处,迈着沉重的步子行至我身侧。可见我没有如往常般与他斟茶,
沈贺舟面色肉眼可见的沉了下来。我仰起脸,将从他书房暗格的信笺一一送至他面前。
“我的信,我家的信,为甚会在你那?”沈贺舟不过眉梢微蹙:“谁准许你动本王的东西的?
”“什么你的东西?那是我爹娘寄给我的信,岏都水患,这么大的事情你都要瞒我,
是想让我爹娘死吗?”“我担心影响你的心情,便没有与你说这事。”轻描淡写的,
他竟就这般揭过去了。可我分明望见他眼底不加掩饰的不耐,
甚至连半句安抚的话都不愿予我,哪怕是哄骗!在他折身之际,我双手皆扒上他的袖摆,
拔高的音调带着破碎的哭腔与无法言喻的心酸,歇斯底的模样活似个疯子。
“你凭什么替我做主!连这般大事,你都要瞒我?!”他皱着眉拂开我揪住他衣袖的手,
似乎不满我的“失态”,语气淡了几分:“就凭我是你丈夫,既入我王府,
那旁的就不应是你该忧心的。”“旁人?那是我爹……”眼泪终控制不住滚落下来,
滚烫地滑过双颊。“阿颜,如今你姓沈。”他弯身掐住我的下颌,
温热的掌一如从前般轻抚过我的眼眉,那笑意依旧温煦,不同的是笑意不曾至眼底,
“本王忍耐有限,你知道的,听话,嗯?”接下来的几日,我与沈贺舟开始冷战。
相互之间谁都不与谁说话,连他去岏都救灾的消息漏进我耳中,
身为淮阳王妃的我竟是最后一个知悉的。来到书房门前时恰与出来的崔宛旖打了个照面,
她瞥我一眼,喉咙逸出声冷哼便绕开我翩然而去。我步入屋室,任由昏黑湮没身躯。
待到双眼适应黑暗,才看清书房内唯有桌案上一盏摇曳将熄的烛。05.“阿颜?你怎来了?
”他望向我时,也分不清那是愧色还是旁的,只听他叹气,温言软语听着像是与我解释,
“我也是前一日接到父皇交与的任务,前往岏都赈灾……”我无声在他身侧跪坐下来,
脑袋轻轻地枕在他膝头。“我想回家。”他额头与我相抵,温热的吐息在眉宇间缱绻,
无声叹息:“岏都水患,你去不安全。”“那崔宛旖呢?”沈贺舟沉默了,于昏暗间,
他沉沉的眸光凝落至我脸上。他自是知晓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尚在思索该如何忽悠我。
也许我合该哭闹一场,可只觉着疲惫,是我先打破了沉寂:“我爹娘在那,我不放心。
”终于他点了头,说:“好,此番出行也顺道探望岳父岳母,可你要跟着我,不能擅自行动。
”王府前去岏都的车马两日后从汴京出发。粮草辎重为求稳妥走了另一条官道,
而一行是我与崔宛旖,我们轻车简从,却碰上了哄抢的难民。车马被围,
沈贺舟正焦头烂额地安抚,试图以身份弹压。可他的话语并不能让饿极的百姓填饱肚子,
他们前仆后继地往车驾涌,手里的武器不过是路旁捡来的石头,又或是随手折来的树枝。
我坐在颠簸的马车内,凉风卷着尘土与砂砾刮在脸颊生疼,种种声音混杂落进耳里,
我只觉着喧嚣聒噪。“让开!这是淮阳王的车驾!”车夫甩着手里的马鞭驱赶,
可他们人太多了,一批接一批的难民往前扑,妄图争夺钻上车马抢夺能活下去的粮食。
可就在此时,原本拥聚的难民如鸟兽散。另一路人马自远处的山岗高处冒头,
先是零星的几个,而后四面八方不断涌现。他们肩头扛着马刀,一声哨声为号,
数十人便从四面八方俯冲而下,瞬间冲散了乌泱泱的难民。
“贺舟……贺舟……”崔宛旖哽咽着,几近绝望地攥着沈贺舟的衣袖。“怎么办啊!
”我那尊贵的王爷夫君,沈贺舟,当机立断就做出了选择。他一手拉过崔宛旖护在怀里,
夺过侍卫手中那唯一的一匹马,他先扶着崔宛旖上马,而后翻身跃上马背,望向我,
语气快得似是怕耽搁了逃命的良辰吉时。“阿颜,你先躲好!等我安顿好宛旖,
稍后便带兵回来救你!”无措间我紧紧攥着他扬起的一袂袖摆,
嗓音早是颤抖不已:“我会死的。”那么一瞬,我真希望他能回头瞧我一眼,
哪怕是分我一点余光都好……可他都没有。我没有哭也没有喊,
只是眼睁睁看着那两抹身影决绝地消失在这乱局之外,
将我与这片绝望一同留给那即将挥落的马刀。马蹄扬起尘土扑了我满脸,
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凿穿了,先是无尽的痛楚,而后才是风呼啸而过的空洞。
06.原来……他来我家乡赈灾带上我从不是念及旧情,不过是为了彰显他王爷的仁德,
顺便让他的宛旖沿途瞧瞧江南风景罢了。周遭的惨叫将我拉回现实。车外,
不知是仆从还是难民的鲜血溅上车窗。橘春攥着我的手,明明怕极,
却仍硬撑压下哭意试图宽慰我:“娘子,殿下他肯定不会丢下娘子的!”我唇角弯起抹笑来,
但大抵比哭还要难看。山匪举着马刀无差别砍杀,哀嚎与呼喊不断。随厮杀声越来越近,
有山匪挑开车帘闯进车内,狞笑着朝我们伸手。我强忍着恐惧摸索到沈贺舟留在车内的短剑,
紧握着剑柄的双手难抑制的发抖,可我还是强撑着把橘春护在身后。可在山贼眼里,
连同反抗都脆弱得似易折刚抽条的枝,非但不以为意反倒哈哈大笑。“哈哈,有个性!
”紧握剑柄的手指甲几乎陷进掌心的软肉,我不会武,
但至少……这把短剑能让我死得稍微体面些许。“滚开!
”随着锋利的剑刃没入血肉“噗嗤”一声闷响,而后是他的痛呼与谩骂,
飞溅开的殷红亦染红了我的衣襟和脸。可我不能停,咬着牙阖紧双目朝其要害处竭力地挥剑。
车厢血气弥漫,许久他没了声息。我睁开眼,护着橘春往后避开那具朝前扑倒的高壮躯体。
外头的打斗声早不知何时歇了,有天光漏入车厢,是沾血的剑挑起车帘,
而剑的另一端握一抹颀长的影掌中,来人微微歪着颈项,逆着光,清越的嗓音如击玉敲冰。
“死了?你杀的?”眸光落在我手中那柄尚还颤抖的短剑上,而后上移,
牢牢地锁住我的眼睛。明明是疑问的话语,却不带半点起伏。
沾血的剑尖又往那山匪躯壳戳了几下,确认彻底死透后,他收了剑。“嗯,厉害。
”他利落地退出车厢,失了支撑的帘幔再次垂落,遮蔽了外间的日光。而他在马车外,
隔着车帘与我说话:“山贼走了。”我们紧随其后跳下马车,放眼去山野辽阔,一如他所言,
山匪见形势不对早退回远处山岗后,如今独余山野间一片的狼藉与横七竖八的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