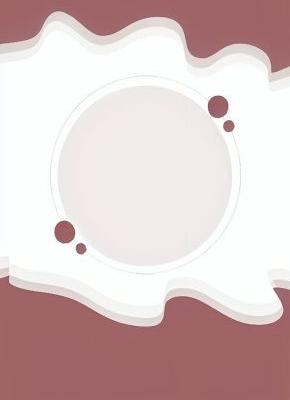十分具有看点的一本爽文《手撕婚书后,我成了天下第一针》,类属于古代言情题材,主人公是陆文渊沈砚,小说原创作者叫做霁色鸢。故事内容丰富多样,充满惊喜与刺激。赶紧仰起头,把那股热意逼回去。窗外,天光大亮。第一幅“闻香绣”,成了。7我把那幅成功的“幽兰”闻香绣仔细包好,递给陆文渊……
章节预览
我绣了三个月,只想听他一句认可。他看了一眼说:“匠气,灵性不足。
”后来他让我把最满意的绣品,送去讨好别人的妾室。我撕了绣品,也撕了婚书。
原来有些人,永远看不懂你心里盛开的花。1最后一针,收线。我捏着细如发丝的绣针,
小心地在背面打了个结,用指甲掐断余线。脖子因为长时间低着头,酸胀得厉害。
我慢慢直起腰,对着烛火,仔细端详案上这幅终于修复如初的传家古绣屏。屏风上的雀鸟,
羽毛根根分明,眼神活灵活现,几乎要从那泛黄的旧缎子上振翅飞出来。为了它,
我在这绣房里闷了整整三个月,对着原样描摹、配色、试针,眼睛都快熬花了。
窗外传来打更的梆子声,三更天了。沈砚还没回来。也好,赶在他回来前弄完了。
我盼着他能看见,能说一句……手心有些汗湿,我在裙子上擦了擦。烛火啪地爆了个灯花,
惊得我心也跟着一跳。小荷轻手轻脚进来,添了次灯油。“**,还不歇息吗?
爷怕是又在外头有应酬了。”“就歇。”我应着,目光却没离开那绣屏。越看,心里越没底。
这里颜色是不是深了点?那里针脚,会不会还是显得紧了?沈砚他……看得上眼吗?
他总是说,我的绣活,差些意思。具体差在哪儿,他又说不明白,
只丢下“匠气”、“灵性”这些词,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门帘终于响了,
带进一阵夜里的凉风和淡淡的酒气。他回来了。我站起身,手指不自觉地蜷缩起来。
“修好了?”他走到案前,身形高大,投下一片阴影,遮住了烛光。“嗯。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干。他俯身,凑近了看。手指虚虚地划过绣面上那只雀鸟的羽毛,
没碰实,怕沾了灰似的。看了半晌,没说话。我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怦怦乱跳。“形是准了,
”他终于开口,声音没什么起伏,“神嘛…”他顿住,侧过头来看我,眉头微蹙着。“阿阮,
你这手艺,匠气还是重了些,灵性不足。”我眼皮猛地跳了几下,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罢了。”他直起身,语气像是宽慰,又像是最终下了定论,
“祖辈的东西,能复原成这个样子,已是不易。你也尽力了。”他转身,朝门外走去,
像是忽然想起什么,在门口停住,没回头,只丢下一句:“赶明儿母亲寿辰,你准备的贺礼,
可别也这般…一板一眼。”门帘晃荡着,他脚步声渐远。我站在原地,没动。
屋子里只剩下烛火燃烧的细微噼啪声。刚才绷得太紧的身体,一点点松懈下来,
却带着一种无处着力的虚软。我低头,看着自己摊开的手掌。那根刚才一直捏着的绣花针,
不知怎么还紧紧攥在指间。针尖深深地抵在掌心的嫩肉上,
留下一个深红的、几乎要沁出血来的印子。密密麻麻的刺痛感,这才迟来地,
清晰地传了过来。匠气。灵性。我慢慢松开手指,绣针掉在桌面上,发出轻微的一声“嗒”。
掌心那个红点,像一颗突兀的朱砂痣,烙在那里。窗外,他的脚步声彻底消失了。夜,
静得可怕。我看着那幅在烛光下华美却莫名显得死气沉沉的绣屏,
再看看自己掌心那点刺目的红。三个月的心血。原来,在他眼里,终究只是一句…匠气过重,
灵性不足。我吹熄了烛火,摸黑走到床边坐下。黑暗中,手心里的那点刺痛,一阵阵,
格外清晰。像根扎进心里的刺。2沈母寿宴那天,沈府热闹得很。
厅里厅外都是来道贺的宾客,言笑喧哗,空气里混着酒菜香和脂粉气。
我捧着那幅新绣的“四季花卉”屏风,深吸了口气,走到主位前。“母亲福寿安康。
这是儿媳一点心意,愿母亲春秋永驻。”我垂着眼,将屏风呈上。沈母脸上挂着得体的笑,
目光在绣屏上扫了一圈,淡淡的。“嗯,有心了。”她摆了摆手,旁边的嬷嬷便上前,
接了过去,随手放在了角落的礼堆里。心,跟着那屏风一起,沉了下去。我退回自己的席位,
指尖有点凉。席间推杯换盏,热闹是别人的。我低着头,小口吃着菜,味同嚼蜡。
耳朵却不由自主地竖着,听沈砚那边说话。他正和几位看起来是文人雅士的客人交谈。
不知怎么,话题就引到了绣活上。“…说起来,女子习绣,陶冶性情便好。
”沈砚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点漫不经心的笑意,刚好能让我这边清晰地听到,
“终究是些女儿家的玩意,难登大雅之堂。”有人附和着点头。
他话锋似有若无地转向我这边,继续说:“阿阮性子静,在这上头是肯下功夫的。不过,
我更望她多学学管家理事,那才是正途。”我捏着象牙筷子的手指,猛地收紧,指节泛白。
那幅被弃置角落的“四季花卉”,上面的迎春、夏荷、秋菊、冬梅,是我琢磨了多久,
才绣出的四季流转,草木枯荣。在他嘴里,就成了…难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心头那点憋屈,
像藤蔓一样缠上来,越勒越紧。“哦?沈公子此言,在下不敢完全苟同。
”一道温和却清晰的声音响起,打断了那片附和之声。众人循声望去,
是坐在末席的一位客人。穿着半旧青衫,面容清癯,听说姓陆,是个被贬谪的京官,
今日似乎是跟着某位大人来的,位置安排得偏。他并未看沈砚,目光落在角落那幅绣屏上,
语气平和却坚定:“我倒觉得,这幅绣品颇有意趣。草木精华,自有乾坤。
这份蕴含其中的生机与灵韵,难得。”席间瞬间静了一下。
所有目光在我、沈砚和那位陆先生之间逡巡。沈砚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脸色肉眼可见地沉了下来。我猛地抬起头,看向那位陆先生。他正好也望过来,
目光清澈平和,对着我,极轻微地颔首示意。那一瞬间,堵在心口的那团棉花,
好像被这轻轻一句话捅开了一个口子。一股酸涩又带着点暖意的情绪涌上来,
冲得我眼眶发酸。我赶紧低下头。宴席还在继续,丝竹声又响起来。但我能感觉到,
落在身上的目光复杂了许多。沈砚后来没再提这茬,但他母亲偶尔瞥过来的眼神,
比刚才更淡,更冷。散席时,人潮涌动。我故意落在后面,听见前面两位夫人低声交头接耳。
“…沈少爷今日这话,说得未免太不留情面…”“可不是嘛,未过门的媳妇,
脸面往哪儿搁…那绣活我看着顶好…”“那位出声的陆大人,
听说是在京里得罪了人才…”“嘘…慎言…”我默默听着,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回到那个精致却冰冷的小院,窗外夜色沉沉。沈砚今晚,大概又不会来了。“草木精华,
自有乾坤…”**在窗边,喃喃重复着那句话。手无意识地在冰凉的窗棂上勾画着绣样。
或许,真的不是我的手艺不行。是这地方,这儿的人,从一开始,就看不懂我。
3沈砚派人来叫我,说有事吩咐。到了前厅,才发现他几位朋友也在。
他指着桌上我前几天刚完工的那幅“青竹图”绣品,语气随意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上官大人新纳了位侧室,听说颇懂些风雅。你这幅绣品,正好给我拿去送个礼,
也显得我们沈家有心意。”我心头猛地一哽。那幅“青竹”,竹叶挺拔,
带着风雨不折的风骨,是我近来最满意的一幅。“这幅…”我吸了口气,尽量让声音平稳,
“…不太合适吧?是依着我的心思绣的,怕不合上官侧室的眼。”“有什么不合适?
”沈砚挑眉看我,带了点不耐烦,“你的绣活,能入上官大人的眼,是你的体面。
”他顿了顿,目光在我脸上转了一圈,像是施舍般补充道,“况且,阿阮,你心里要清楚。
以你的出身,将来即便进了门,做了正室,终究还是差些火候。
如今提前用这些绣品打点些关系,对你没坏处。”差些火候。正室。打点关系。这几个词,
像淬了冰的针,一根根扎进我耳里,扎进心里。原来如此。原来在他心里,
我根本就不配做他沈砚的正妻。我的绣品,我的心血,也只配拿去讨好别人的妾室。
一直以来积压的所有委屈、不甘、隐忍,在这一刻,被这句话彻底点燃,
烧掉了最后一丝犹豫。脑子里那根绷了太久的弦,“铮”地一声,断了。
我看着他那张写满理所当然的脸,再看看旁边那些或带着同情、或纯粹看戏的眼神。
血液好像瞬间冲到了头顶,手脚却一片冰凉。我上前一步,什么也顾不上了,
一把抓起那幅“青竹图”。“嘶啦——”清脆的裂帛声,猛地炸响在寂静的厅堂里。
精美的绣品从中裂开,丝线崩断,竹子的风骨被粗暴地撕成两半。满座皆惊。
抽气声此起彼伏。沈砚“嚯”地站起来,脸色铁青:“阿阮!你疯了!你做什么!
”我没理他。把撕成两半的绣品狠狠扔在地上。像扔掉什么脏东西。然后,
我从怀里掏出那封一直贴身收着的婚书。那红纸黑字,曾经承载过多少小心翼翼的期盼,
此刻却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手心发疼。“嘶啦——”婚书也应声而裂,
变成两片无用的废纸。我抬起头,直视着沈砚那双惊怒交加的眼睛,声音出奇的平静,
却带着一种豁出一切的冰冷和清晰:“我的技艺与真心,不是你沈家可以随意轻贱的。
”碎片飘飘悠悠,落在地上。像我的心,曾经那么小心地捧给他们,现在,彻底碎了,
也不要了。我转身,再没看他们任何人一眼,挺直了背,
径直走出了这间富丽堂皇却让人窒息的前厅。身后是死一般的寂静,然后,
爆发出沈砚震怒的吼声和一些劝解的人声。我都听不清了。跨出门槛,外面天光刺眼,
晃得我眼睛发疼,几乎要流出泪来。可心里头,那块压了不知道多久的大石头,
好像随着那两声“嘶啦”,轰然落地了。空荡荡的。却也,轻快了。我知道,从今往后,
我和这沈家,再没半点干系了。4从沈府出来,身上就那身衣裳,还有个小包袱,
里面几件贴身物品和仅有的几件绣品。天大地大,竟不知该往哪儿去。
在街上漫无目的走了半天,腿像灌了铅。以前出门不是马车就是轿子,
从没觉得这京城街道这么长,这么吵。路过以前常给沈家送绣活的铺子,掌柜的看见我,
眼神躲闪,赶紧低下头算账。我懂了。沈家打过招呼了。心里那点因为决裂生出的痛快,
很快被现实的冷风吹得干干净净。天黑下来,没地方去,只能摸到城西那座废弃的龙王庙。
角落里堆着些干草,我就缩在那儿,抱着膝盖,听着外面野狗叫,一夜没合眼。第二天,
肚子饿得咕咕叫。我拿出包袱里绣得最好的一幅帕子,走到离破庙不远的一个小市集。
找块干净点的石头,把帕子铺开。人来人往,没人停下看一眼。站了大半天,
太阳晒得头发晕。一个提着菜篮的大婶经过,瞥了一眼。“哟,绣得真不赖。”她说着,
脚步却没停。“大婶,您看看…”我鼓起勇气开口,声音干涩。她摆摆手,
“不当吃不当穿的,谁买这个呦。”又冷又饿,我缩回破庙,数了数身上仅有的几个铜板,
只够买两个最便宜的粗面馍馍。啃着干硬的馍,嗓子眼堵得厉害。以前在沈家,再不受待见,
也没吃过这种东西。就这么过了两三天,一幅绣品都没卖出去。这天下午,我刚把绣品摆开,
两个穿着邋遢、流里流气的男人就晃了过来。“小娘子,新来的?在这儿摆摊,
问过我们兄弟没有?”其中一个咧着嘴,露出一口黄牙。我心里一紧,把包袱往怀里拢了拢。
“我…我就卖点绣活,不占地方。”“绣活?”另一个凑近了,一股酸臭气扑面而来,
“让哥哥看看,绣的什么好东西?”他的手作势就要往我脸上摸。“走开!
”我猛地后退一步,后背撞在冰冷的墙上,声音发颤。“嘿,还挺辣!”黄牙嬉笑着逼近,
“没钱也行,陪哥哥们玩玩…”绝望像冰水一样从头浇到脚。我紧紧攥着包袱,
指甲掐进手心,比针扎还疼。难道刚出狼窝,又要…“光天化日,欺凌弱女,
二位好大的威风。”一个清朗的男声在不远处响起。那俩地痞动作一僵,
回头骂道:“哪个不长眼的…多管闲事…”我循声望去,
看见一个穿着半旧青衫的身影立在巷口,逆着光,看不清脸,但身姿挺拔。
黄牙似乎掂量了一下,啐了一口:“算你走运!”两人骂骂咧咧地走了。我腿一软,
顺着墙壁滑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心跳得像要蹦出来。脚步声靠近,在我面前停下。
我惊魂未定地抬头。逆光散去,看清了那张清癯温和的脸。是寿宴上那位,说过“草木精华,
自有乾坤”的陆先生。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惊讶,只有一种沉静的了然,
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他怎么会在这里?5**着墙壁,腿还软着,仰头看他。“陆先生?
”他微微弯腰,伸出手:“还能起来吗?”我犹豫了一下,没搭他的手,
自己撑着墙慢慢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包袱还紧紧抱在怀里。“多谢先生解围。
”我低声道谢,心里却绷着一根弦。他怎么偏偏出现在这儿?“举手之劳。”他收回手,
神色自然,目光落在我怀里的包袱上,“阿阮姑娘,是在售卖绣品?
”我下意识把包袱捂得更紧。“…是。不过,没人买。”他沉默了一下,
环顾四周这脏乱的巷口。“此地不是说话之处。前面有个茶摊,还算清净,可否借一步说话?
”我跟他走到巷子口的茶摊,挑了个最角落的位置。他要了两碗最便宜的茶。茶水粗涩,
我小口抿着,等他开口。他从我摊开的包袱里,拿起一方绣了兰草的帕子,仔细看着,
手指轻轻拂过叶片。“线条流畅,形态舒展…”他顿了顿,看向我,“更重要的是,这兰草,
有风骨,有韧性。灵气藏在针脚里,并非匠气。”我捏着茶碗的手一抖。灵气…这个词,
从沈砚嘴里出来是贬斥,从他嘴里出来,却像是…真的看懂了。“沈公子看的是规矩,
是形制。”他仿佛看穿我的心思,放下帕子,语气平和,“我看的,是里面的‘活气’。
草木精华,并非虚言。”我心里有点乱,分不清他是真的懂,还是另有所图。
“陆先生到底想说什么?”“我想与你合作。”他直视我的眼睛,说得清晰直接,
“我略通些药理香道。我在想,若能以特制香料浸染丝线,再行刺绣,使绣品不仅可观,
亦可闻香,清心宁神。谓之‘闻香绣’。”以香入绣?我愣住了。这想法…闻所未闻。
“你的绣工已有灵韵根基,若再辅以香韵,必是锦上添花。”他语气笃定。
我却猛地想起沈砚那些话,还有他母亲冷淡的眼神。心又冷了下来。“陆先生说笑了。
我如今的身份…只怕会连累先生。况且,这等新奇玩意儿,未必有人认。
”他摇摇头:“我找你,与沈家无关,与你的过往无关。只与你的手有关。
”他从袖中取出一个小银锭,推到我的面前。“这是定金。”我看着那锭银子,
足够我租个小屋,安稳生活一两个月。心头警铃大作。“…为什么帮我?”他看着我,
眼神清澈,没有任何躲闪或施舍的意味。“我不是沈砚。”他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我赌的,是你的才华,以及我的眼光。”才华。眼光。这两个词砸在我心上,沉甸甸的,
带着一种陌生的暖意。我看着那锭银子,又看看他坦然的脸。戒备还在,
但心底那股快要熄灭的火苗,好像被这句话,轻轻吹动了一下。我伸出手,
慢慢地将那锭银子握在手心。冰凉的触感,却莫名烫人。6用陆先生给的定金,
在城南租了间临街的小屋子,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安顿下来第一件事,
就是把他给的几种安神香料拿出来研究。把香料磨成极细的粉末,
按他说的法子调进染线用的水里。线浸进去,捞出来,颜色是染上了,
可味道…要么淡得闻不见,要么一晾干就散没了。我不信邪。又重新调比例,
换了一种基础线材,再试。一整天,就对着那几个盆盆罐罐折腾。
屋里弥漫着各种香料混杂的气味,熏得人头晕。手指被染得五颜六色,
还带着一股洗不掉的药草味。第一批线晾干了,我赶紧穿针试绣。针脚下去,香味没出来,
反而因为线材处理过,变得有些脆硬,绣出来的花瓣边缘毛糙,失了往日的灵动。不行。
拆了重来。又试。把香料混进蜂蜡里,试图裹在线上。结果线变得黏糊糊,根本没法用,
针都穿不过去。再试。用蒸煮的法子想让香味渗透…锅烧干了,差点把屋子点着,
一锅线也废了。几天过去,陆先生给的香料耗掉一小半,
桌上堆满了失败的线团和绣坏了的布片。钱也花出去不少,买了各种不同的丝线、棉线来试。
晚上躺在床上,浑身酸疼。脑子里全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线和沈砚那句“匠气过重,
灵性不足”。他是不是说对了?我是不是根本就不是这块料?离了沈家,我其实什么都不是?
看着所剩无几的钱和一堆废品,心里慌得厉害。把脸埋进被子里,真想就这么算了。
把剩下的银子还给陆先生,承认自己不行。可…“我赌的,是你的才华,以及我的眼光。
”陆先生那句话突然冒出来。还有他放下银子时,那双清亮的眼睛。我不能就这么认了。
天还没亮,我又爬起来。对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光,
看着桌上最后一点香料和仅剩的一种极细的素白丝线。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是不是太贪心了?总想着让香味浓烈持久。或许…换个路子,只要一丝似有若无的香气,
反而更勾人?我重新磨了香料,这次只取最精华的部分,用量减到最少,
用特别温和的油慢慢浸透丝线,不再追求速成,只求一点点、慢慢地渗进去。处理完,
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我拈起那根浸润好的丝线,它在晨光里泛着极淡的润泽。屏住呼吸,
穿针,引线。针尖落在绷好的绢面上,绣的是一株空谷幽兰。一针,一线。屋子里很静,
只有针穿过绢布的细微声响。我绣得极其小心,几乎是凭着本能。当最后一瓣兰花瓣完成,
我放下针,下意识地凑近绣面,轻轻嗅了一下。一股极清、极淡,却无比清晰的幽兰冷香,
丝丝缕缕,钻入鼻尖。不是花香,是带着青草和泥土气息的,一株活生生的兰草的味道。
我愣住了,用手背用力揉了揉眼睛,再凑过去闻。香味还在。稳稳地,从绣线里散发出来。
成了。真的成了。我看着绢面上那株悄然绽放的幽兰,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鼻子一酸。
赶紧仰起头,把那股热意逼回去。窗外,天光大亮。第一幅“闻香绣”,成了。
7我把那幅成功的“幽兰”闻香绣仔细包好,递给陆文渊。“陆先生,
你看…这个真能卖出去吗?”他接过,打开看了一眼,又轻轻嗅了下,点点头。“放心。
”他带我去了城东一家叫“雅集斋”的铺子,店面不大,但看着清雅,
来往的也多是一些文人打扮的客人。他跟掌柜的低声谈了几句,掌柜的接过绣品,仔细端详,
又凑近了闻,脸上露出惊异的神色。“这…这香味…”“寄卖。”陆文渊言简意赅,
“价钱…”掌柜的沉吟一下,报了个数。我听了心里一跳,那价钱,
抵得上我以前在沈家绣好几个月的工钱。陆文渊却摇摇头,伸出三根手指。“这个数。
”掌柜的倒吸一口气:“陆先生,这…”“就这个数。”陆文渊语气平和,却不容置疑。
我们把绣品留在那儿,约好三天后去看情况。那三天,我坐立难安,
时不时就走到雅集斋附近,远远看着,又不敢进去。第二天下午,陆文渊来找我,
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走吧,去雅集斋。”我心里七上八下地跟他去了。
刚走到店门口,就听见里面有些喧闹。“掌柜的!那幅带香味的兰花绣屏,真没了?
”“是啊,李公子,您来晚一步,早上就被王学士家的夫人买走了。”“哎呀!我出双倍!
你帮我问问,还能不能订?”“这…我得问问那位绣娘…”我们走进去,
掌柜的一看见陆文渊,立刻迎了上来,脸上堆满了笑:“陆先生!您可算来了!
您看这…”他指着原本放绣屏的空位,周围还围着两三拨人,都在打听。
“那位绣娘…可否再绣几幅?价钱好商量!”一个穿着富贵的公子急切地说。“是啊是啊,
这闻香绣,真是奇了!挂在书房,满室清雅!”掌柜的把我们请到内间,搓着手,
兴奋地说:“陆先生,阿阮姑娘,你们也看到了。一幅根本不够卖!王夫人买回去,
据说在她家诗会上出了大风头,好几位夫人都派人来问呢!您看…”他拿出一个钱袋,
推到陆文渊面前。“这是卖得的银子,按您说的价,一分不少。”陆文渊把钱袋推到我面前。
“她的工钱。”我拿着那沉甸甸的钱袋,手有点抖。这么多…真的卖出去了,
还是这么高的价钱。从雅集斋出来,我还觉得像在做梦。街上的喧闹声都变得不真实了。
“这下,可以安心了?”陆文渊侧头看我。我用力点头,鼻子有点酸,但心里是满的。
第一次,靠自己的手艺,挣来了这么多,得到了真心的夸赞。我们把银子存进了钱庄。
看着那张薄薄的银票,我才有了点真实感。消息像长了翅膀。没过两天,
连我住的那条小街都有人在议论,说城南出了个厉害的绣娘,绣的花儿带着真香味,
卖得极贵。这议论自然也飘进了沈府。沈砚在书房听着小厮的禀报,嗤笑一声,
将手里的书丢在桌上:“哗众取宠的玩意儿。看她能得意几时。”8好日子没过几天,
风头就变了。先是雅集斋的掌柜偷偷找来,面带难色:“阿阮姑娘,陆先生,
这几日有些不好的话在传…”“说什么?”我心里咯噔一下。
“说…说咱们这绣品的香味闻久了头晕,怕是用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熏的…”接着,
我发现自己出门时,街坊邻里看我的眼神有点怪,以前常打招呼的几个大婶也躲着走。
预定绣品的单子,莫名其妙退了两张。陆文渊听完,没说什么,只是眉头微微蹙起。第二天,
他让我带上一幅新绣的“秋菊”闻香绣,又去了雅集斋。他也没进内间,就在店铺大堂里,
让掌柜的把绣品摆在显眼处。他则搬了把椅子坐在旁边,气定神闲地喝茶。果然,
没多久就有个生面孔的汉子晃进来,指着绣品大声说:“就这东西?听说香味有问题,
可别害人!”店里其他顾客都看了过来,交头接耳。陆文渊放下茶杯,站起身,
走到那汉子面前,语气平静:“这位兄台,何处听来的谣言?
”那汉子眼神闪烁:“大家都这么说!”陆文渊不再理他,转向店内众人,
声音清晰:“诸位,在下陆文渊,不才,曾在太医院任职数年。”此话一出,满堂皆惊。
太医院!那可是给宫里贵人看病的!“这绣品所用香料,皆由我亲自挑选配制。
”他拿起那幅“秋菊”,坦然递向众人,“皆是《本草拾遗》、《千金方》中明确记载,
具有安神定惊、舒缓心绪之效的草木精华。诸位若不信,可当场验看,
亦可寻任何一位靠谱的大夫鉴别。”他目光扫过那造谣的汉子,语气依旧平和,
却带着分量:“若说此物有害,莫非宫中所用香药,亦有不妥?”那汉子脸一白,
支吾着说不出话,灰溜溜地挤出门去了。店内顿时议论开来。“原来是陆太医!怪不得!
”“我就说嘛,这香味闻着舒服得很!”“太医亲自配的香,
绣娘巧手制成…这可是‘医绣双绝’啊!”“掌柜的!这幅菊花给我包起来!”一场风波,
就这么被陆文渊轻描淡写地化解了。不仅谣言不攻自破,
“医绣双绝”的名头反而借着这机会传开了。雅集斋的生意比以前更红火,
订单又雪片般飞来。我看着他沉静的侧脸,心里那块大石头彻底落了地。第一次觉得,
有这么个人在身边,好像再大的难处,也不怕了。消息很快传开。沈砚在茶楼雅间里,
听着手下人战战兢兢地回报,说陆文渊如何当众验看,如何引经据典,
如今“闻香绣”和“医绣双绝”的名声如何响亮。他手里的茶杯越捏越紧,指节泛白,
脸色铁青,猛地将茶杯掼在地上,摔得粉碎。9“我在想,若香气也能分层次,
如同画中的远近虚实。”陆文渊指着桌上新处理的几种丝线,“比如绣荷花,
初绽的、盛放的、乃至将谢的,气味是否可略有不同?”我眼睛一亮,立刻接上:“对!
初夏的荷,带着点青涩的水汽,盛放的则浓郁些,
将谢时又有点淡淡的干枯气息…我怎么没想到!”“我们可以试试用不同浓度的浸染,
或者混合几种相近的香料…”他拿起一支小毫,蘸了点清水,在纸上轻轻勾勒调配的比例。
我凑过去看,鼻尖几乎要碰到他的衣袖,能闻到上面沾染的、极淡的药材清苦气,
混着此刻满屋的试验香料的复杂气息。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
对着那些丝线、香料和绣样讨论开来。窗外天色不知不觉暗下来,小荷进来点了灯,
又悄悄退出去。我们谁也没提吃饭的事。他有时会引一句医书里的香药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