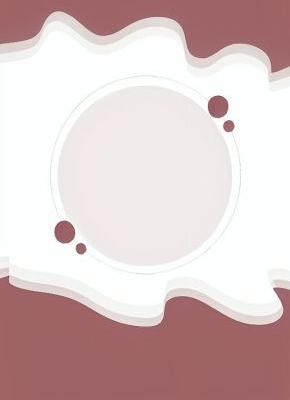《娇养病质子:太女她独占成瘾》是陌喃林最新创作的一部短篇言情小说。故事中的楚清辞秦昭身世神秘,具备异于常人的能力,他们展开了一段离奇又激烈的旅程。这本小说紧张刺激,引人入胜,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奇幻和冒险的世界。两名穿着东宫内侍服饰的太监悄无声息地上前,一左一右,站在了仍在咳嗽的楚清辞身旁,……。
章节预览
大渊,天启二十三年冬。第一场雪来得早,也来得急,不过一夜,
便将整座帝都永安覆上一层沉甸甸的银白。皇宫深处,飞檐斗拱都失了棱角,
唯余一片肃杀的素净。风卷着雪沫,掠过宫墙夹道,发出呜呜的咽鸣。
楚清辞就是在这个清晨,被带进大渊皇宫的。
他身上是南楚使臣能凑出的、最体面的一套月白色锦袍,却依旧单薄得可怜,
料子在北地干冷的空气里显得僵硬而突兀。寒风无孔不入,从宽大的袖口、领襟钻进去,
带走皮肤上仅存的热气。他走得慢,脚步虚浮,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又像随时会被下一阵风刮倒。苍白的面容几乎要与身后的雪墙融为一体,唯有那双眼睛,
沉寂得如同深潭古井,映不出半点天光雪色。身后跟着两名大渊的宫廷侍卫,甲胄摩擦,
步伐沉重,与他轻飘飘的足音形成鲜明对比。没有催促,也没有搀扶,只不远不近地跟着,
如同押解。穿过一道又一道巍峨的宫门,越往深处,殿宇越是恢弘,守卫越是森严。
楚清辞垂着眼,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浅淡的阴影,掩去了所有情绪。
他知道目的地是哪里——麟德殿,大渊皇帝召见使臣与藩属的重要场所。今日,
他这个南楚送来的“礼物”,或者说,“抵押品”,要在那里被正式呈递。南楚积弱,
北疆战事接连失利,不得不向大渊称臣纳贡。除了岁币、丝绸、茶叶,还需送一位王子为质,
以示诚意。他是南楚王第九子,母亲出身低微,早逝,在宫中无依无靠,
是最合适、也最无足轻重的那个。殿前的广场空旷得让人心慌,积雪已被清扫,
露出冰冷的青石板。从广场到高高的殿阶,还有很长一段路。楚清辞停下脚步,微微喘息,
冰冷的空气吸入肺腑,激起一阵压抑的咳嗽。他掩住口,
肩胛骨在单薄的衣料下突出清晰的形状,整个人像一枚即将被风吹折的芦苇。
殿内隐约传来乐声与模糊的谈笑,那是属于胜利者的喧嚣。他闭了闭眼,重新抬步。
踏上第一级台阶时,靴底湿滑,他身子几不可察地晃了一下。侍卫的手似乎动了一下,
终究没有伸过来。他稳住自己,继续向上。一级,两级……每一步都耗去他不少力气,
额角渗出细密的虚汗,被风一吹,寒意直透骨髓。终于到了殿门前。沉重的殿门敞开着,
里面灯火通明,暖气混着酒气、熏香气扑面而来,与外面的酷寒像是两个世界。
殿内人影幢幢,衣香鬓影,珠光宝气。引路的太监尖细的嗓音响起:“南楚质子,楚清辞,
觐见——”所有的声音,乐声,谈笑声,似乎在那一刻低了下去,无数道目光,
好奇的、审视的、怜悯的、轻蔑的,齐刷刷地落在门口那个苍白单薄的身影上。
楚清辞深吸一口气,迈过高高的门槛。他依照礼制,向着御座的方向,一丝不苟地行下大礼。
动作有些迟缓,但姿态标准。“南楚楚清辞,叩见大渊皇帝陛下,陛下万岁。”声音不高,
带着久病的微哑,却清晰,在骤然安静的大殿里,莫名有些扎耳。御座上的大渊皇帝秦渊,
年近五旬,面容威严,只是眼下带着纵欲后的青黑。他随意地摆了摆手,
目光在楚清辞身上扫过,像看一件无关紧要的摆设。“平身。南楚王的诚意,朕知道了。
赐座。”座位在靠近殿门的下首,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楚清辞谢恩,起身,走向那个位置。
又是一阵头晕目眩,他强撑着坐下,指尖冰凉,悄悄蜷缩进袖中。殿内气氛重新活跃起来,
舞姬甩着水袖翩跹而入,丝竹之声再起。楚清辞低垂着眼,
盯着面前案几上金杯中晃动的琥珀色酒液,酒香浓烈,却引不起他丝毫欲望。他只觉胸闷,
寒意从骨头缝里往外渗。他成了这繁华盛宴里一道沉默的布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
无人与他交谈,他也乐得无人打扰。时间在熏香和乐声中黏稠地流淌。不知过了多久,
殿门处似乎有些动静。原本有些松弛的气氛,莫名地凝滞了一瞬。连御座上的皇帝,
都微微坐直了身体。楚清辞若有所感,抬起眼。一个身影逆着殿外雪地的微光,走了进来。
那是个女子。很高,甚至不逊于殿中许多男子。一身玄色绣金凤的宫装,裙摆曳地,
行走间并无寻常宫眷的袅娜,反而带着一种刀锋出鞘般的利落与压迫。乌发绾成高髻,
只簪一支赤金衔珠凤钗,凤口垂下的东珠,随着她的步伐,在她额间轻晃,映着殿内烛火,
流转着冰冷的光泽。她的面容极美,却是一种极具侵略性的美。眉眼深邃,鼻梁高挺,
唇色是饱满而凌厉的正红。最慑人的是那双眼睛,眼尾微微上挑,看人时,目光沉静而直接,
没有任何迂回与温存,仿佛能穿透皮肉,直视人心。她一路行来,两旁侍立的宫人无声跪伏,
原本谈笑的官员们噤了声,微微垂首。连那些旋转的舞姬,都下意识地放缓了动作,
避开她的路径。大渊皇太女,秦昭。皇帝唯一的嫡女,
也是目前最有权势、最得倚重的继承人。她十五岁监国,手段雷霆,政绩斐然,
却也因性情冷酷、说一不二,令朝野又敬又畏。秦昭并未理会那些目光,径直走到御阶之下,
略一躬身:“父皇。”“昭儿来了。”皇帝语气平常,却隐隐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退让,
“赐座。”太女的座位,设在御座左下首,仅次于皇帝。她坐下,早有宫人无声奉上热茶。
她接过,并未饮用,指尖漫不经心地摩挲着温热的杯壁。她的到来,
像一块巨石投入看似平静的湖面。殿内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喧嚣刻意压低,
目光有意无意地飘向御阶之上那对天家父女,又飞快地移开。楚清辞重新低下头。
这位太女殿下,与他无关。然而,那存在感实在太强。即使垂着眼,他也能感觉到一道目光,
冰冷、审视,如同实质,越过殿中重重人影,落在了他身上。他身体几不可察地绷紧了。
丝竹声不知何时又换了一曲,更显柔靡。有官员起身向皇帝和太女敬酒,说着吉祥话。
秦昭偶尔举杯示意,大部分时间,她的视线,似乎一直定格在某个方向。终于,一曲既终,
短暂的安静间隙。一个带着酒意的声音响起,是坐在楚清辞斜对面的一位大渊宗室子弟,
年轻气盛,脸上带着醉醺醺的笑,指着楚清辞的方向,声音不大不小,
刚好能让附近几桌听见:“啧,南楚……就送来这么个病秧子?瞧那脸色,白的跟纸糊似的,
别还没开春就……哈,那南楚王的脸面可往哪儿搁?”低低的哄笑声响起,夹杂着几句附和。
楚清辞握着袖口的手指,微微收紧。指甲陷进掌心,带来细微的刺痛。他依旧垂着眼,
仿佛什么都没听见。那宗室子弟见他不应,似乎觉得无趣,又或许是酒意上头,
竟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端着酒杯,朝他走了过来。“哎,质子殿下,”他走到楚清辞案前,
居高临下,酒气喷涌,“远来是客,我敬你一杯!怎么,不给面子?”楚清辞抬起眼,
平静地看着他:“在**弱,不胜酒力,请见谅。”“体弱?”那人嗤笑一声,
伸手就去拿楚清辞面前那杯一直未动的酒,“到了大渊,就得守大渊的规矩!这杯酒,
你喝也得喝,不喝……”他的手没能碰到酒杯。一只骨节分明、涂着鲜红蔻丹的手,
凭空伸了过来,稳稳地截住了他的手腕。那手的主人,不知何时已离开了上首的座位,
无声无息地站在了他们旁边。玄色的衣袖上,金线绣成的凤凰在烛火下流光溢彩,
几乎刺痛人眼。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连呼吸声都似乎被冻住了。
那宗室子弟醉意瞬间醒了大半,脸色刷地白了,
结结巴巴:“太、太女殿下……”秦昭没看他。她的目光落在楚清辞脸上。距离很近。
楚清辞能清晰地看到她眼底深处毫无温度的审视,还有那种全然掌控、不容置喙的强势。
她身上有极淡的冷香,像雪后松针,混合着权力的凛冽味道。她松开了那宗室子弟的手腕,
仿佛掸去一粒灰尘。然后,在满殿死寂的注视下,她微微倾身。冰凉的手指,
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捏住了楚清辞的下巴。强迫他抬起脸。指尖的寒意瞬间穿透皮肤。
楚清辞被迫迎上她的目光。那双凤眸里,映着他苍白如雪的脸,
和他眼中瞬间掠过却未能完全藏住的惊悸与屈辱。她的拇指,轻轻擦过他失色的下唇。
动作带着一种狎昵的评估意味。然后,她开口了。声音不高,甚至算得上平静,却字字清晰,
砸在落针可闻的大殿里,砸在每一个人心上。“这么个美人,”她顿了顿,
目光梭巡过他脸上每一寸,像在鉴赏一件脆弱的瓷器,“死了可惜。”死寂。
连御座上的皇帝,都只是看着,没有出声。那宗室子弟早已瘫软在地,抖如筛糠。
楚清辞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这一刻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成冰。
下巴上的手指冰冷而牢固,他挣脱不得,也无法移开视线。只能任由她打量,评估,宣判。
秦昭松了手。失去了钳制,楚清辞控制不住地偏过头,剧烈地咳嗽起来,
苍白的脸颊因窒息和剧烈的情绪波动泛起不正常的潮红,单薄的肩膀颤抖着,
仿佛下一秒就要散架。秦昭直起身,目光淡淡扫过殿中诸人,最后落回楚清辞身上,
语气依旧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即日起,南楚质子楚清辞,移居东宫偏殿。
”“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打扰。”说罢,她不再看任何人,转身,
玄色凤袍划过一道凛冽的弧度,径自向殿外走去。
两名穿着东宫内侍服饰的太监悄无声息地上前,一左一右,站在了仍在咳嗽的楚清辞身旁,
姿态恭敬,却不容拒绝。殿内依旧鸦雀无声。直到太女的身影消失在殿门外,
那股无形的压力才骤然一松。窃窃私语声如同潮水般涌起,
人的目光都复杂地投向那个角落——惊愕、不解、怜悯、幸灾乐祸……楚清辞咳得眼前发黑,
耳中嗡嗡作响。秦昭最后那句话,却异常清晰地烙印在他脑海里。东宫……偏殿?他茫然地,
被两名东宫内侍半扶半“请”地搀扶起来,带离了这座金碧辉煌、却让他倍感寒冷的麟德殿。
殿外的风雪,似乎更急了。东宫。偏殿名为“听竹轩”,名字雅致,位置却僻静,
离太女秦昭所居的正殿“昭阳殿”不算远,只隔着一片不大的竹林。此刻竹林覆雪,
沙沙作响。殿内陈设简洁,但一应俱全,地面铺着厚厚的绒毯,
角落里的鎏金铜兽炭盆烧得正旺,暖意融融,与外面冰天雪地截然不同。
空气里浮动着淡淡的药香和一股清冽的、属于秦昭身上的冷松气息。楚清辞被安置在这里,
已经三日。那日离开麟德殿后,他便直接被带到了此处。两名太医紧随而至,为他诊脉,
开方。苦涩的药汁每日按时送来,由东宫派来的、一个名叫“碧荷”的沉默宫女服侍他喝下。
衣食住行,无一不精,无一不周到。可这周到,更像是一种严密的囚禁。
殿门外永远有侍卫值守,
殿内除了碧荷和定时来诊脉的太医(太医来时必有东宫管事太监陪同),他见不到任何人。
不允许踏出殿门半步,连在廊下站一站,都会立刻有人“恭请”他回屋,说是风雪严寒,
恐伤了贵人玉体。楚清辞大部分时间,只是靠在窗边的软榻上,看着窗外被雪压弯的竹枝,
沉默。秦昭没有再来。但那日麟德殿上,她指尖的冰冷,她目光的逡巡,
她那句“死了可惜”,却日夜盘旋在他心头,带来一种比病体更沉重的不安。
他不知道这位以冷酷专断闻名的大渊太女,究竟意欲何为。是真的只是“惜才”?
还是另有所图?抑或只是一时兴起的玩弄?他就像一个被困在华美笼中的雀鸟,
等待着主人下一次心血来潮的临幸或处置。第四日,傍晚。雪停了,天色阴沉,压得很低。
炭盆里的银骨炭偶尔爆出轻微的噼啪声。楚清辞刚喝完药,碧荷无声地退下。他靠在榻上,
胸口熟悉的憋闷感又泛上来,他忍耐着,没有咳嗽出声,只是呼吸变得有些急促。
殿门就在这时被推开了。没有通报,没有脚步声先至。只有一股裹挟着外面寒意的风,
和那道玄色的身影。秦昭走了进来。她似乎刚从外面回来,
肩头还落着未曾拂尽的、细碎的雪晶。玄色大氅下,依旧是那身标志性的凤纹宫装,
只是发髻上的珠钗换了一支更简洁的玉簪。她挥手,
殿内侍立的碧荷和原本在角落里的管事太监立刻躬身,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并带上了门。
殿内只剩下他们两人。炭火的热气,药汁的苦味,她身上清冽的冷香,还有那股无形的压力,
瞬间充满了整个空间。楚清辞下意识地想要起身行礼,却被一阵更猛烈的咳嗽打断。
他捂唇侧身,咳得蜷缩起来,额角青筋隐现。秦昭就站在那里看着他,没有走近,
也没有说话。直到他咳声渐歇,虚脱般靠在引枕上喘息,她才动了。她走到炭盆边,
拿起一旁的铜火箸,漫不经心地拨弄了一下炭火。跳跃的火光映亮她半边侧脸,明暗不定。
“太医的药,不管用?”她问,声音平淡,听不出情绪。楚清辞拭了拭嘴角,
低声道:“回殿下,已好多了。只是旧疾,一时难除。”秦昭放下火箸,转身,走到软榻前。
她站得近,阴影笼罩下来。楚清辞不得不仰头看她。
她的目光落在他因咳嗽而泛红潮湿的眼角,又滑到他没什么血色的唇上,最后定格在他脸上。
“南楚,”她忽然开口,语气像是随意提起,“冬日也这么冷么?”楚清辞一怔,
不明白她为何问这个,只得如实回答:“南楚……冬日湿冷,不如北地酷寒。
”“湿冷……”秦昭重复了一遍,伸出手。楚清辞身体几不可察地一僵。
那只手没有碰他的脸,而是掠过他的肩头,落在了他搭在榻边的手上。他的手很凉,
即使在温暖的室内,也像一块冰。秦昭的手却是温热的,甚至有些烫。她握住了他的手,
力道不重,却完全包裹住。陌生的触感,温热,干燥,带着常年握笔或握剑留下的薄茧。
楚清辞指尖猛地一颤,想缩回,却被握得更紧。“手这么凉,”秦昭语气依旧平淡,
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炭火不够?”“不……够的。”楚清辞声音有些干涩。
他的手在她掌心,僵硬得不知所措。那种被全然掌控的感觉,比在麟德殿被捏住下巴时,
更甚。秦昭没再说什么,只是握着他的手,似乎想用自己的体温去煨热它。她的拇指,
无意识地在他冰凉的手背上轻轻摩挲了一下。那一下,让楚清辞几乎要跳起来。
一种难以言喻的战栗,从被她触碰的皮肤,瞬间窜遍全身。不是恐惧,也不完全是厌恶,
是一种更加混乱、更加无助的感觉。时间在寂静中流淌,只有炭火偶尔的轻响。
不知过了多久,秦昭松开了手。楚清辞几乎立刻将手缩回袖中,指尖蜷缩,
那残留的温热触感却挥之不去。秦昭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深,
似乎要看到他竭力维持平静的表象下去。“好好养着。”她说,听不出是命令还是别的什么。
然后,她转身,像来时一样突兀地离开了。殿门开合,带进一丝冷风,很快又被暖意吞没。
楚清辞独自留在骤然空旷下来的殿内,良久,缓缓抬起那只被握过的手,放在眼前。
手背上似乎还残留着那烫人的温度和薄茧的粗糙感。他闭上眼,胸口那股憋闷,不知为何,
更重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听竹轩成了楚清辞全部的世界。秦昭并非每日都来,
但每隔两三日,总会出现在这里。有时是傍晚,有时是深夜。她来了,有时只是站一会儿,
看看他喝的药渣,或者探手试一下他额头的温度(她的手指总是微凉,
落在皮肤上激起一阵轻栗),有时会问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
比如“睡得可好”、“饭菜合口否”,得到他简短而恭谨的回答后,便不再多言。
她的话一直不多,存在感却强得惊人。她来时,整个听竹轩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
所有宫人噤若寒蝉,连呼吸都放轻。她离去,那种无形的压力才会缓缓消散。楚清辞的身体,
在太医的调理和东宫无微不至的照料下,竟真的有了些起色。咳喘发作的次数少了些,
面色也不再是那种濒死般的惨白,偶尔会有一丝极淡的血色。但他心头的迷雾,
却一日重过一日。秦昭对他,与其说是“宠”,
不如说是一种极度偏执的“控制”和“占有”。药必须当着她或她指定的心腹面喝完,
一滴不许剩。送来的衣物用具,她有时会亲自过目。有一次,
一个刚调来听竹轩不久的小太监,在服侍楚清辞用膳时,不小心将一点汤水溅到了他袖口,
小太监吓得立刻跪下请罪。这事不知怎的传到了秦昭耳中,当夜,那小太监就被调走了,
再也没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沉默、举止近乎刻板的碧荷和另一名年长的宫女。
她似乎不允许任何一点可能的“意外”发生在他身上,
也不允许任何旁人(除了她指定的人)过于靠近他。这种控制密不透风,令人窒息。
楚清辞试图从碧荷口中探听一点外面的消息,哪怕只是关于南楚的只言片语。
但碧荷如同哑巴,除了必要的请示回话,绝不开口。他就像被困在一口温暖的深井里,
抬头只能看到东宫这一方被竹林切割的天空。直到那一日。那是他被囚于东宫的第二个月末。
天气依旧严寒,但积雪开始消融,檐下滴滴答答落着水。秦昭是午后来的,
脸色似乎比平日更冷峻些,眉宇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戾气。她进来时,楚清辞正坐在窗下,
手里拿着一卷从东宫书库借来的、无关紧要的地理志,却没有看进去。她挥退了碧荷,
走到他面前,忽然伸手,抽走了他手中的书卷。楚清辞抬头,对上她的目光。
今日她的眼神格外幽深,像结了冰的湖面下涌动的暗流。“想看南楚的风物志么?”她问,
声音听不出喜怒。楚清辞心头一跳,垂下眼:“不敢。只是随手翻阅。
”秦昭将那卷书随手丢在旁边的案几上,发出“啪”的一声轻响。她俯身,
双手撑在软榻的扶手上,将他困在方寸之间。那股冷冽的香气强势地包裹了他。“是不敢想,
”她的气息拂在他耳畔,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金属摩擦般的质感,“还是不能想?
”楚清辞屏住呼吸,指甲深深掐入掌心。他不知该如何回答。
秦昭凝视着他骤然绷紧的侧脸线条,和他微微颤动的睫毛,忽然笑了。那笑意很浅,
未达眼底,反而更添寒意。“你心里,是不是日夜盼着,南楚有人来接你回去?或者,
盼着南楚强盛起来,让你这个质子,能有点用处?”每一个字,都像冰锥,扎进楚清辞心里。
他脸色更白,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可惜,”秦昭直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目光里有一种近乎残忍的了然,“你等不到了。”她从袖中取出一封薄薄的绢书,
丢在他膝上。“自己看。”楚清辞手指颤抖着,拿起那封绢书。
是大渊安插在南楚的探子传回的消息简报,上面墨迹犹新。寥寥数行字,却如惊雷,
在他眼前炸开。南楚王病重,卧床不起。三王子与五王子为夺储位,兵戎相见,
都城郢都已陷入混乱,波及数州。边境守将亦有异动……内乱。他的故国,
在他为质的这段时间里,非但没有获得喘息之机,反而陷入了更深的泥潭。父王病重,
兄弟阋墙,生灵涂炭……而他,远在千里之外,困于敌国储君的深宫,无能为力。
绢纸从他指间滑落,飘落在厚毯上,无声无息。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胸口传来熟悉的绞痛,喉咙里涌上腥甜,他死死咬着牙,将那口血气压了回去。
眼前阵阵发黑,耳边嗡嗡作响。秦昭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冰冷而清晰:“你现在,除了我这里,无处可去。”“安心待着。”她看了他最后一眼,
那眼神复杂难辨,然后转身离开。殿门关上。楚清辞终于支撑不住,伏在榻边,
剧烈地咳嗽起来,这一次,他没能压住,殷红的血点溅落在素色的衣袖和毯子上,触目惊心。
碧荷悄无声息地进来,看到血迹,脸色微变,却依旧没有说话,只是迅速而熟练地收拾,
又端来温水让他漱口,换下弄脏的衣物。楚清辞任由她摆布,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
暮色四合,残余的雪光映在他眼底,一片死寂的灰白。南楚……内乱。
他最后的、渺茫的指望,似乎也断了。那一夜,听竹轩的灯,很晚才熄。而昭阳殿的方向,
灯火通明,直至天明。接下来的日子,楚清辞如同失了魂。他依旧按时喝药,用膳,
但人肉眼可见地迅速消瘦下去,刚刚养出来的一点活气荡然无存。
他常常整日整日地坐在窗边,望着外面融雪的竹林,一言不发,
眼底是深不见底的沉寂与绝望。秦昭来的次数,似乎多了些。有时深夜才来,
身上带着夜露的寒气,有时还隐约能闻到极淡的酒气。她来了,常常只是站在他榻边,
沉默地看着他。那目光沉甸甸的,压得楚清辞几乎喘不过气。她不再问话,
他更不会主动开口。两人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冰冷的屏障。直到那晚,
南楚内乱详细战报传来的夜晚。风声鹤唳的消息最终被证实,三王子在郢都巷战中落败,
五王子暂时控制都城,但各地藩王、将领不服,南楚已陷入事实上的分裂与战乱。
大渊边境将领紧急奏报,请示方略。这个消息,楚清辞是偷听到的。
两个送炭盆来的小太监在廊下低声交谈,语气带着事不关己的唏嘘和隐约的兴奋。
他们以为殿内的质子殿下已经睡了。楚清辞躺在榻上,睁着眼,听着那细碎的、残忍的话语,
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刀子,凌迟着他的心脏。故国烽火,家国破碎,亲人相残……而他,
在这里,被当成金丝雀豢养。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混合着绝望、悲愤、不甘,
在他冰冷死寂的心湖里,掀起了滔天巨浪。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夜已深,
雪不知何时又下了起来,开始只是细碎的雪粒,渐渐变成鹅毛大雪,纷纷扬扬,覆盖了庭院,
压弯了竹枝。听竹轩内寂静无声。碧荷在外间歇息。值守的侍卫在廊下,
偶尔传来轻微的跺脚声。楚清辞悄无声息地起身。他没有披大氅,只穿着单薄的寝衣。
足袜踩在冰凉的地板上,寒意瞬间窜遍全身。他推开内室的门,走过外间,
碧荷似乎睡得很沉,没有动静。他轻轻拉开殿门。风雪呼啸着扑面而来,
瞬间打湿了他的头发和单薄的衣衫,冰冷刺骨。他赤着脚,踩进了殿外厚厚的积雪里。冷。
刻骨铭心的冷。从脚底直冲天灵盖,冻得他牙齿格格打战,几乎瞬间失去了知觉。
但他没有停。他一步一步,朝着昭阳殿的方向走去。雪很深,没过他的脚踝,
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冰冷的雪水浸透了他的足袜和裤脚,寒气如毒蛇般顺着腿蜿蜒而上。
他要去找她。他要问个明白。他要……求她。求她放他走。哪怕只有一线希望,
哪怕回去是死路一条,他也要回去。死,也要死在故国的土地上,而不是在这里,
做一个无知无觉、任人摆布的傀儡和玩物!风雪迷住了他的眼睛,
窒息般的寒冷让他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痛。他踉跄着,摔倒在雪地里,又挣扎着爬起来。
寝衣很快被雪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沉重而冰冷。头发上、眉毛上,都结了一层白霜。
视线开始模糊,意识也开始涣散。只有那个念头,还在支撑着他。昭阳殿的轮廓,
终于在漫天风雪中显现出来。殿内灯火通明,映着飞舞的雪花,恍如幻境。
殿前的侍卫发现了他,惊愕地想要阻拦,却见他状若癫狂,赤足散发,在雪地里蹒跚而行,
一时竟愣住了。楚清辞用尽最后力气,扑倒在昭阳殿前冰冷的石阶下。积雪被砸出一个浅坑。
他抬起头,望着那扇紧闭的、威严的殿门,嘶哑的、破碎的声音,用尽全力喊了出来,
混合在风雪的呜咽里:“楚清辞……求见太女殿下!
”“求殿下……开恩……放我……归国……”声音在空旷的殿前回荡,很快被风雪吞没。
他伏在雪地里,身体因为寒冷和激动而剧烈颤抖,意识一点点抽离。眼前的灯火开始摇晃,
重叠。殿门,终于开了。明亮的暖光倾泻而出,勾勒出一个高挑的玄色身影。秦昭站在门口。
她似乎也未曾安寝,长发未束,披在肩后,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玄色寝衣,赤着双足。
她看着台阶下,雪地里,那个几乎被白雪覆盖、蜷缩颤抖的身影。他抬起头,脸上毫无血色,
嘴唇冻得青紫,睫毛上凝着冰晶,唯有那双眼睛,在看到她时,
迸发出最后一点绝望的、倔强的光亮。秦昭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一步一步,走下台阶。
赤足踩在冰冷的、未扫的积雪上,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她走到楚清辞面前,蹲下身。
风雪在她周身飞舞,玄色的衣袂和长发在风中纠缠。她伸出手,没有碰他的脸,
而是直接穿过他的腋下和膝弯,将他从冰冷的雪地里,打横抱了起来。
楚清辞身体僵硬冰冷得像一块石头,轻得几乎没有重量。秦昭抱着他,转身,
一步步走回殿内。她的手臂很稳,怀抱却并不温暖,甚至因为刚从温暖的室内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