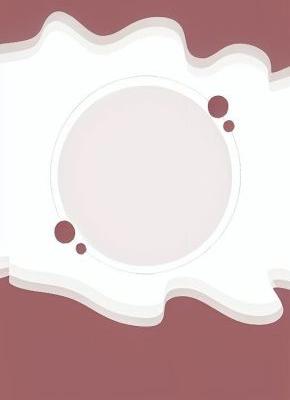在归雁,破晓中,陈砚之沈清如是一位充满魅力和坚定的人物。陈砚之沈清如克服了生活中的挫折与困难,通过努力与坚持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邵北笙024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紧凑的情节,将陈砚之沈清如的成长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挂着“庆祝胜利”“光复南京”的红纸标语。路边的小摊上,卖着鸭血粉丝汤、梅花糕,热气腾腾的香气飘过来,勾着人的食欲。沈清如……必将给读者带来无尽的感动和启示。
章节预览
1汽笛划破长夜民国三十四年八月的风,终于吹走了北平城上空盘旋了八年的阴霾。
永定门火车站的月台上,攒动的人头像是洇在宣纸上的墨团,推搡着、喧嚣着,
却又在某一刻突然静下来——远处传来的汽笛声,拖着长长的尾音,刺破了午后沉闷的空气。
陈砚之踮着脚,扒开身前攒动的人群往铁轨方向望。他的长衫下摆被汗水濡湿,贴在腿上,
手里攥着的那张皱巴巴的车票,边缘已经被指尖的汗渍浸得发潮。八年了,从南京到重庆,
再从重庆辗转回北平,这趟路他走了整整八年,如今终于要踏上归途,
去见那个他在梦里念了千百遍的人。月台上的广播断断续续响着,夹杂着电流的滋滋声,
内容无非是庆祝抗战胜利、列车即将进站之类的话。可陈砚之没心思听,
他的目光死死钉在铁轨延伸的尽头,直到那抹黑色的车头轮廓一点点清晰,
直到车轮碾过铁轨的哐当声越来越近,他的心脏才跟着那节奏,一下下擂鼓似的跳起来。
列车停稳的瞬间,月台上的人群爆发出一阵哄笑与哭喊交织的声响。
有人举着写满名字的纸牌,有人伸长了脖子往车窗里探,还有人干脆趴在车窗边,
对着里面喊着亲人的名字。陈砚之被挤在人群中间,往前挪了两步,又被后面的人推回来,
他索性站定,目光扫过一节节车厢的窗户。突然,他的视线顿住了。倒数第三节车厢的窗边,
坐着一个穿蓝布旗袍的女人。她的头发梳得整齐,用一根银簪绾着,侧脸对着窗外,
鼻梁挺直,下颌线柔和。哪怕隔着拥挤的人群和蒙着灰尘的车窗,
陈砚之还是一眼认出了她——是沈清如。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抬手,想要喊她的名字,
可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一点声音。八年的时光,像是一把钝刀,
把他原本流利的话语、炽热的思念,都磨成了哽在喉头的砂砾。沈清如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转过头,目光穿过人群,落在了陈砚之的脸上。四目相对的刹那,
她手里捧着的那本线装书“啪”地掉在腿上,眼里先是闪过一丝错愕,随即,
一层薄薄的水汽漫了上来。陈砚之终于挤出人群,跑到车厢门口。列车员正在验票,
他把手里的车票递过去,指尖还在颤抖。“麻烦,我找沈清如,
她在里面……”列车员看了他一眼,又往车厢里瞥了瞥,笑着摆摆手:“胜利了,团聚了,
快上去吧!”他踩着摇晃的车厢踏板进去,一步步走向沈清如的座位。
周围的乘客都在笑着、聊着,没人注意到这对久别重逢的人。他站在她面前,看着她抬起头,
眼里的泪终于落了下来,顺着脸颊滑进嘴角。“砚之……”她开口,
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你回来了。”陈砚之蹲下身,握住她放在膝盖上的手。
她的手很凉,指腹上有一层薄薄的茧,想来是这八年里操持家务留下的痕迹。“我回来了,
清如。”他的声音也带着哽咽,“我答应过你的,一定会回来。”八年之前,
南京城破的前夜,他拉着她的手站在秦淮河畔,对岸的炮火映红了半边天。他说:“清如,
我要跟着学校撤去重庆,你等我,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回来娶你。”那时她哭着点头,
把自己绣的平安符塞在他怀里,说:“我等你,哪怕等十年、二十年,我都等。”如今,
十年未至,八年已满,他终于站在了她的面前。车厢里的广播又响了起来,
这次是清晰的歌声——《松花江上》的旋律,却被唱得带着几分欢喜。
沈清如捡起掉在腿上的书,是他当年留在南京的《漱玉词》,书页已经泛黄,
上面还有他当年批注的字迹。“我一直带着它,”她说,“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总觉得你就在我身边。”陈砚之看着那本书,眼眶更热了。他想起在重庆的那些日子,
躲在防空洞里批改学生的作业,夜里听着轰炸声睡不着,就靠着记忆里她的模样,
一笔一划地写她的名字。那些写满名字的信纸,如今都被他妥帖地收在行李箱里,
那是他熬过八年岁月的唯一支撑。列车缓缓开动,离开北平站,朝着南京的方向驶去。
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往后退,北平城的城墙、胡同、老槐树,都渐渐模糊。
沈清如靠在他的肩上,听他讲着这八年的经历:在重庆的防空洞里躲轰炸,
在油灯下给学生上课,在听说芷江受降的消息时,
和同事们抱在一起哭……她也讲着自己的日子:南京沦陷后,她躲在城南的老巷子里,
靠着给人绣东西换口粮,日本人挨家挨户搜查的时候,她把他的照片藏在鞋底,
差点被发现;听说抗战胜利的消息那天,她跑到秦淮河畔,对着河水哭了一下午,
像是要把八年的委屈都哭出来。“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她轻声说,“有时候夜里听见炮声,
就怕你……”“我不会的,”陈砚之打断她,握紧她的手,“我答应过你的事,一定会做到。
”夕阳透过车窗照进来,落在两人交握的手上,镀上一层温暖的金光。
车厢里的人们还在聊着天,说着各自的重逢与期盼,那些细碎的话语,
和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成了这胜利之日里,最动听的旋律。
2秦淮河畔的旧影列车抵达南京站的时候,已是三天后的清晨。
出站口的人潮比北平站还要汹涌,举着横幅的、敲锣打鼓的、相拥而泣的,
处处都是胜利的喜悦。陈砚之牵着沈清如的手,慢慢走出车站,
脚下的石板路还是记忆里的模样,只是路面上多了些战争留下的坑洼。“先去我家吧,
”沈清如说,“我爹娘还在城南的老宅子等着呢,他们一直惦记着你。”陈砚之点点头。
他记得沈家的老宅子,在秦淮河畔的乌衣巷附近,是一座带天井的四合院。当年他常去那里,
和沈老先生讨论文史,听沈清如在院子里弹琵琶。那些日子,
是他这辈子最安稳、最美好的时光。两人沿着中山路往前走,沿途的店铺大多已经重新开张,
挂着“庆祝胜利”“光复南京”的红纸标语。路边的小摊上,卖着鸭血粉丝汤、梅花糕,
热气腾腾的香气飘过来,勾着人的食欲。沈清如买了两块梅花糕,
递给他一块:“你以前最爱吃这个,记得吗?每次来我家,都要让巷口的张婶给你做。
”陈砚之咬了一口,甜糯的口感在嘴里化开,还是记忆里的味道。
只是当年陪他吃梅花糕的姑娘,如今眼角已经有了淡淡的细纹,这让他心里泛起一阵酸涩。
八年的时光,终究还是在彼此身上留下了痕迹。走到乌衣巷口,远远就看见沈家的老宅子了。
院门敞开着,门口挂着两个红灯笼,沈老先生和沈太太正站在门口张望。看见他们走来,
沈太太立刻迎了上来,拉着沈清如的手,又看向陈砚之,眼眶一红:“砚之,你可算回来了!
这些年,苦了你了。”“伯母,让您和伯父担心了。”陈砚之躬身行礼,声音里满是愧疚。
当年他离开南京时,沈老先生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照顾自己,清如就交给你了,
等你回来,我把她亲手交到你手里。”如今,他总算没有食言。沈老先生拄着拐杖走过来,
看着陈砚之,点了点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抗战胜利了,咱们中国人的腰杆,
又挺直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却透着一股历经劫难后的坚定。走进院子,
天井里的那棵桂花树还在,只是枝叶比当年稀疏了些。沈清如说:“日本人占了南京的时候,
这棵树差点被他们砍掉,我爹拼死护住,才留了下来。”陈砚之伸手摸了摸树干,
粗糙的树皮上有一道深深的砍痕,像是一道伤疤,刻在这棵树的身上,
也刻在这座城市的记忆里。午饭的时候,沈太太做了满满一桌子菜,
有陈砚之爱吃的盐水鸭、糖醋排骨,还有沈清如拿手的素炒青菜。席间,
沈老先生说起这八年的经历:日本人闯进宅子搜查,抢走了家里的字画和藏书,
他带着家人躲在阁楼里,靠着藏起来的粮食度日;沈清如为了给家里换口粮,
白天去给人绣活,夜里偷偷教邻居家的孩子读书,生怕被日本人发现。“清如这孩子,
苦了八年啊,”沈太太抹着眼泪说,“多少人劝她改嫁,她都不肯,说一定要等你回来。
”陈砚之看向坐在身边的沈清如,她低着头,脸颊微红。他握住她的手,放在桌下,
轻声说:“辛苦你了,清如。”她抬起头,眼里带着笑:“不辛苦,只要你回来,
就什么都值了。”饭后,沈清如带着陈砚之去了秦淮河畔。八年不见,
秦淮河的水还是那样缓缓流淌,只是河面上的画舫少了许多,岸边的楼阁也有些破败。
他们沿着河岸慢慢走,走到当年他和她告别时的那座石桥上。“还记得吗?那天晚上,
你就在这里和我说,要去重庆。”沈清如靠在桥栏上,望着河水说。“记得,
”陈砚之站在她身边,“那天你哭了,我却连替你擦眼泪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我怕自己一回头,就舍不得走了。”“我知道你必须走,”她说,“国难当头,
你们这些读书人,总要做点什么。我只是担心,担心你在路上出事,
担心你在重庆吃不饱、穿不暖。”他想起在重庆的一个冬天,天气格外冷,
他身上只穿着一件薄棉袄,夜里冻得睡不着。就在那时,他收到了沈清如寄来的包裹,
里面是一件厚厚的棉衣,还有几双她绣的袜子,包裹里夹着一张字条:“砚之,天冷添衣,
勿念。”那张字条,他一直带在身上,直到现在。“我收到你寄的棉衣了,”他说,
“那年冬天,全靠它才熬过来的。”沈清如笑了:“我就知道你会冷,
南京的冬天比重庆暖和,你肯定不习惯那边的气候。”夕阳西下,
把秦淮河的水染成了金红色。远处传来了孩童的嬉笑声,还有小贩的吆喝声,
那些久违的、充满烟火气的声音,让这座饱经战火的城市,重新活了过来。“砚之,
”沈清如转过身,看着他,“我们结婚吧。”陈砚之愣住了,随即,
一股巨大的喜悦涌上心头。他握住她的肩膀,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好,我们结婚。
就在南京,就在这秦淮河畔,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她踮起脚尖,轻轻靠在他的怀里,
听着他的心跳声。八年的等待,八年的期盼,终于在这一刻,有了归宿。
秦淮河的风拂过他们的脸颊,带着桂花的香气,像是在为这对久别重逢的恋人,
送上最温柔的祝福。3旧宅里的新声决定结婚的消息传开后,
沈家的院子里顿时热闹了起来。沈太太忙着找人布置新房,
沈老先生则翻出了家里珍藏的老酒,说要在婚礼上好好喝几杯。陈砚之也忙前忙后,
修补着院子里破损的桌椅,擦拭着落满灰尘的门窗,仿佛要把这八年里积攒的力气,
都用在装点这座即将成为他们新家的宅子上。这天下午,
陈砚之正在天井里擦拭那张老旧的八仙桌,忽然听见院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抬头一看,
是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手里提着一个布包,站在门口张望。“请问,
这里是沈先生家吗?”男人开口问道,声音里带着几分拘谨。陈砚之放下抹布,
走上前:“是的,我是沈先生的女婿,请问您找他有事?”男人愣了一下,
随即笑了:“女婿?那太好了!我是城东中学的校长,姓李。抗战前,我和沈先生是旧识,
听说他老人家平安,特地过来看看。”沈老先生听到声音,从屋里走出来,看见李校长,
眼睛一亮:“是景文啊!你还活着,太好了!”两人紧紧握手,眼眶都红了。原来,
李校长和沈老先生都是南京师范学堂的同学,抗战爆发后,两人失去了联系。
李校长带着城东中学的学生撤到了安徽,辗转多年,直到胜利后才回到南京,
四处打听沈老先生的消息,这才找到这里。“沈先生,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
”李校长坐下后,喝了口茶,认真地说,“城东中学在战争中被毁得差不多了,如今胜利了,
我想重新把学校办起来。只是师资短缺,听说你当年的学生陈砚之回来了,他是学国文的,
能不能请他来学校任教?”陈砚之愣了一下,他倒是没想过任教的事。在重庆的八年里,
他一直在流亡学校里教书,对三尺讲台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如今回到南京,
能在一所安定的学校里教书,倒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沈老先生看向陈砚之:“砚之,
你的意思呢?”陈砚之沉吟片刻,点了点头:“李校长,我愿意去。抗战胜利了,
孩子们不能再没有书读,我们这些读书人,总要为国家的将来做点什么。
”李校长大喜过望:“太好了!有你加入,城东中学就有希望了!我明天就派人去整修校舍,
争取下个月就开学。”送走李校长后,沈清如走到陈砚之身边,笑着说:“看来,
你又要重操旧业了。”“是啊,”陈砚之握住她的手,“在重庆的时候,我就想着,
等胜利了,一定要在南京办一所像样的学校,让孩子们能安安稳稳地读书。如今,
总算是有机会了。”接下来的日子里,陈砚之每天都去城东中学帮忙整修校舍。
学校的围墙被炸塌了大半,教室的窗户也都碎了,桌椅更是东倒西歪。
他和工人们一起搬砖、砌墙、修理桌椅,手上磨出了血泡,却一点也不觉得累。
沈清如也常常过来帮忙,给工人们送水、送点心,闲暇时就坐在尚未修好的教室里,
看着陈砚之忙碌的身影。有一次,她看见陈砚之在黑板上写下“少年强则国强”几个大字,
阳光透过破损的窗户照在他身上,让她想起了当年在南京中央大学的课堂上,他也是这样,
站在讲台上,眼里闪着光,给学生们讲着家国大义。开学前的最后一天,
陈砚之把教室的最后一张桌椅摆放整齐。他站在教室门口,看着焕然一新的校舍,
心里充满了欣慰。这时,沈清如走过来,递给他一个布包:“这是我给你做的教案夹,
以后上课用得着。”陈砚之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个用蓝布做的夹子,上面绣着一枝梅花,
针脚细密,格外精致。“谢谢你,清如。”他把夹子抱在怀里,像是抱着一份沉甸甸的希望。
第二天,城东中学正式开学了。校门口挂着“欢迎新同学”的横幅,孩子们背着书包,
蹦蹦跳跳地走进校园,一张张稚嫩的脸上,满是对知识的渴望。陈砚之站在讲台上,
看着台下的学生,清了清嗓子:“同学们,今天是我们城东中学开学的日子,
也是我们告别战争、迎接和平的日子。从今天起,我们在这里读书、学习,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他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窗外的阳光洒进来,
落在孩子们的脸上,也落在他手里的教案夹上。沈清如站在教室门外,听着他的话语,
嘴角扬起一抹温柔的笑。她知道,这才是陈砚之想要的生活,也是这座城市在历经劫难后,
最需要的希望。4婚礼上的泪光婚礼定在十月初十,那是沈老先生特意找先生算的好日子,
说是“宜嫁娶,百无禁忌”。离婚礼还有半个月,沈家的院子里就已经挂满了红灯笼,
沈太太更是每天都要清点一遍嫁妆,嘴里念叨着:“清如从小就懂事,这下总算嫁个好人家,
我也放心了。”陈砚之的父母在抗战中病逝于老家,如今他在南京无亲无故,
沈老先生便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操持着婚礼的大小事宜。
他翻出了自己年轻时的长袍马褂,改了改尺寸,给陈砚之穿上:“当年我娶你伯母的时候,
穿的就是这件,如今传给你,也算圆满了。”陈砚之穿上长袍马褂,站在镜子前,
看着镜中的自己,忽然觉得有些恍惚。八年之前,他还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
如今却已是历经沧桑的中年人。但好在,他终于可以给沈清如一个名分,给她一个安稳的家。
婚礼前的几天,秦淮河畔的画舫也渐渐多了起来。陈砚之租了一艘最大的画舫,
打算在婚礼当天,带着沈清如和亲友们游河。他记得沈清如最喜欢秦淮河的夜景,
说那是“天下最美的风景”,如今,他要把这最美的风景,作为送给她的新婚礼物。
婚礼当天,沈家的院子里挤满了宾客。有沈老先生的旧友,有城东中学的同事和学生,
还有巷子里的街坊邻居。陈砚之穿着长袍马褂,胸前戴着大红花,站在院门口迎接宾客。
沈清如则坐在新房里,由伴娘陪着,头上盖着红盖头,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吉时一到,
迎亲的队伍敲锣打鼓地出发了。陈砚之牵着红绸的一端,另一端系在沈清如的手上,
两人并肩走着,穿过热闹的街巷,走向秦淮河畔的画舫。沿途的百姓都笑着鼓掌,
有人喊着:“新婚快乐!”“早生贵子!”那些温暖的话语,让这对新人的心里充满了甜蜜。
登上画舫,宾客们纷纷落座。沈老先生站起身,端起酒杯:“今天,
是小女清如和陈砚之大喜的日子。八年抗战,我们熬过了最黑暗的岁月,如今迎来了和平,
也迎来了这对孩子的幸福。我在这里,敬大家一杯,也祝这对新人,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宾客们纷纷举杯,掌声雷动。陈砚之牵着沈清如的手,站起身,向众人鞠躬道谢。
他看着沈清如,她的红盖头已经被掀开,露出了那张熟悉的脸庞,眼里闪着泪光,
却笑得格外灿烂。画舫缓缓驶离岸边,秦淮河的夜景在眼前铺展开来。
岸边的灯火倒映在水里,随着波纹晃动,像是撒了一河的星星。沈清如靠在陈砚之的肩上,
看着窗外的风景,轻声说:“砚之,你看,秦淮河的夜景,还是和当年一样美。”“是啊,
”陈砚之搂住她的肩膀,“以后每年的今天,我都带你来游河,看遍秦淮河的春夏秋冬。
”这时,有宾客提议让新人唱首歌。陈砚之想了想,拉起沈清如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