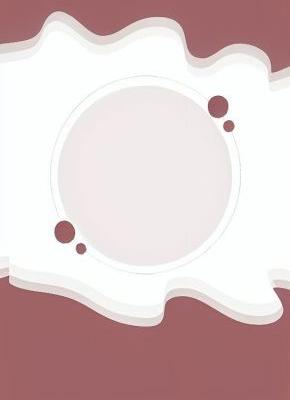在东书恒的笔下,《广陵禁曲》成为一部引人入胜的短篇言情作品。主角孤桐广陵散谢停云的命运曲折离奇,通过独特的视角和精彩的情节展开,引发读者对人性、命运等深刻的思考。本书以其扣人心弦的叙述方式和丰富多彩的情感描写而闻名。常于月夜弹《广陵散》,声极悲怆,闻者断肠。忽一夜,曲未终而声绝。次日,村人见其僵坐琴前,十指尽裂血染弦,目眦尽裂而亡。所……。
章节预览
那把琴送来时,已是子夜。我本不该在此时抚琴,更不该去碰那首曲子。但我是个琴师,
一个快要活不下去的琴师。京城里认得老桐木、认得好手艺的人,越来越少。送琴来的,
是个面生的古董贩子,姓黄,精瘦,眼珠子转得活。“顾师傅,您给瞧瞧,这琴,
”他压低声音,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沾着古气儿呢,听说前朝宫里流出来的。”琴身乌黑,
断纹是漂亮的蛇腹断,龙池上方刻着两个小字:“孤桐”。确是古物,寒气森森。指尖一触,
冰得我一哆嗦。“夜里别试,尤其别试《广陵散》。”黄贩子临走,倚着门框,
回头说了这么一句,嘴角似笑非笑。我没问为什么。行里古怪的忌讳多。可那夜,
我喝了太多劣酒。债主的脸在眼前晃,还有病榻上老母亲断续的咳声。我看着“孤桐”,
心里涌起一股邪火,一股破罐子破摔的狠劲。凭什么不能弹?我倒要听听,这琴配上那绝响,
能怎样。我净了手,点燃一柱线香。烟气笔直上升,屋内死寂。我坐下来,
手指搭上冰冷的弦。第一个音迸出。嗡——不像是我弹的,倒像是琴自己醒了,
发出的是一声深长、幽怨的叹息。我指尖发颤,酒醒了大半。可手却停不下来。
《广陵散》的旋律,带着积压了千百年的愤懑与杀伐,从我指下倾泻而出。**,更黑了。
弹到“冲冠”一段,激越处,我浑身汗毛倒竖。不是错觉。我听见了另一个声音。不是琴音。
是呼吸。极其轻微,缓慢,悠长,就紧贴在我右耳后。一下,一下。我的琴声没停。
那呼吸声也没停。它跟着我的节奏,我的快慢,我的起伏。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人,
正与我鼻尖相对,静静聆听,一同沉浸在这肃杀的曲调里。冷汗,顺着我的脊梁沟往下淌。
我猛地收手。琴音骤歇。那呼吸声,也停了。死一样的寂静包裹了我。只有线香燃尽的灰,
无声跌落在香炉里。我僵坐着,不敢回头。直到窗外传来第一声鸡鸣。那东西,
好像……走了。我瘫在椅子上,里衣尽湿,像从水里捞出来。我知道,
我惹上不该惹的东西了。第二天,我发了高热。昏沉中,尽是破碎的琴音和那贴耳的呼吸。
母亲挣扎着给我熬了姜汤。她什么也没问,只是用枯瘦的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叹了口气。
黄贩子下午来了。他站在门口,不进来,上下打量我。“顾师傅,脸色可不太好。
”我盯着他:“那琴,怎么回事?”他干笑两声:“能怎么回事?老物件,有点脾气。
您……昨晚试了?”我没答。他了然地点点头,从怀里摸出几块银元,放在门边破凳上。
“琴钱,尾款。您收好。那琴,您留着玩吧。”说完转身就走。“站住!”我撑着门框,
“把话说清楚!”他回头,眼神闪烁:“说什么?规矩我提醒过您了。夜里别弹《广陵散》。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尤其用那把‘孤桐’。它……招东西。喜欢听,
喜欢跟着弹。不把弹琴的人耗干,它不走。”“什么东西?”“琴魂。
”黄贩子吐出两个字,快步消失在巷子口。琴魂。我看向屋内静静躺着的“孤桐”。
它此刻温顺无害。病稍好,我便去了城西的茶馆。那里是三教九流混迹之地,
也是消息最杂的地方。我找到一个常年收售旧乐器、外号“孙瞎子”的老头。他其实不瞎,
只是眼神浑浊。我隐去“孤桐”和夜间弹奏的事,只问:“孙爷,听说过‘琴魂’吗?
夜里弹《广陵散》会招来的那种。”孙瞎子捏着茶碗的手顿了顿,浑浊的眼珠转向我,
看了好一会儿。“你碰上了?”我心里一紧:“听人说起,好奇。”他放下茶碗,
慢悠悠:“《广陵散》,嵇康绝响,曲意孤高愤慨,煞气重。夜里阴气盛,弹这曲子,
容易引来不干净的东西共鸣。有些古琴,年头太久,经手的人杂,心思不净的,或者横死的,
魂啊念啊,就附在琴上。它们忘不了曲,尤其忘不了《广陵散》。你夜里弹,
就像给它开了门,请它进来。它听得高兴,就跟你和鸣。你怎么停?”“停下会怎样?
”“停下?”孙瞎子古怪地笑了笑,“你停了,它还没尽兴呢。它会帮你接着弹。
用你的手,你的精气神。直到你手指磨烂,心血耗干,油尽灯枯。
”我后背发凉:“没法子送走?”“难。”孙瞎子摇头,“它缠上的是你的‘音’。要么,
你永远不再碰琴。要么,你找到比它更强的‘音’,压过它,或者……满足它。
”“怎么满足?”“那就得知道,跟着你的是个什么‘东西’,它要什么了。
”孙瞎子凑近些,压低声音,“小子,我看你印堂发暗,眼神飘忽。实话告诉我,
是不是已经请回家了?”我沉默。他叹了口气:“自求多福吧。记着,天黑之后,
千万别再碰那曲子。琴,最好也封起来。”我失魂落魄地回家。封琴?**什么活下去?
夜里,我跪在母亲床前。“娘,儿子可能……惹了麻烦。”母亲咳嗽着,
摸索着握住我的手:“桐儿,娘耳朵还没聋。昨晚……那琴声不对,不止你一个人在弹。
你心里怕,是不是?”我点头,喉咙发哽。“娘没什么见识,”她缓缓说,“但知道一个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那东西要是讲理的,你试试跟它讲讲理。
要是不讲理……”她用力捏了捏我的手,“我顾家的儿子,也不能任人拿捏。”跟它讲理?
我苦笑。深夜,我独自坐在外间,看着用黑布蒙起来的“孤桐”。四周寂静。然后,
我听到了。极轻微的,指甲刮过琴弦的声音。噌……一声。两声。它在催促。
2我开始做噩梦。梦里总在弹琴,弹那首《广陵散》。弹到手指渗血,疼痛钻心,
却停不下来。身边总有个模糊的影子,很近,我能感到它冰冷的“注视”和那同步的呼吸。
有时影子似乎想露出面目,却总隔着一层雾。白天我精神萎靡,几次调弦都走了音。
债主上门,我把黄贩子给的银元大半还了债,剩下的抓了药。家徒四壁。唯一的活计,
是给城北一户办寿宴的人家,在堂会上弹几支喜庆的曲子。宴席那日,
我带上自己常用的另一张琴。主家热闹,觥筹交错。我坐在角落,
弹着《良宵引》《平沙落雁》。人们吃喝谈笑,没几个人认真听。弹到一半,
我忽然感到一阵极冷的视线。不是来自宾客。我猛地抬头。透过月亮门,
看到后院僻静的廊下,不知何时,放着一张琴。乌黑的琴身,蛇腹断纹。是“孤桐”!
它怎么会在这里?我心跳如鼓。琴旁空无一人。但我感觉到,那东西,那个“琴魂”,
就在这里。它在听。我指尖一滑,一个刺耳的走音迸出。谈笑声静了一瞬。有人皱眉看过来。
我强自镇定,接了下去。寿宴终于结束。我拿到微薄的酬劳,几乎是逃离了那座宅院。
回家路上,天已擦黑。穿过一条窄巷时,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不紧不慢,跟着我的节奏。
我快,它快。我慢,它慢。我猛地转身。巷子空空荡荡。只有远处一点昏黄的灯火。
我汗毛倒竖,快步往家跑。推开家门,我愣住了。“孤桐”好好地躺在屋里桌上,蒙着黑布。
似乎从未离开。母亲从里间出来:“怎么了?脸色这么白。”“娘,咱们这院子,
今天有谁进来过?”“没有啊。我一整天都在里屋躺着,没听见动静。”它不仅能跟出来,
还能自己回去。这不是缠上琴。这是缠上我了。夜里,刮起了风。窗户纸呜呜作响。
我睁着眼躺在床上,不敢睡。外间,传来了清晰的琴音。是《广陵散》的开头。弹得很慢,
很生涩,仿佛一个初学的人在笨拙地摸索。但每一个音,都极准,极冷。我捂住了耳朵。
琴音却像直接钻进了脑子。它弹得很耐心,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开头的几句。它在练习。
用我的琴,在我的家里。我浑身冰冷,愤怒却一点点压过恐惧。我猛地起身,冲到外间。
琴音停了。“孤桐”静静躺在月光里,黑布落在一旁。屋里只有我粗重的呼吸声。
“你到底想怎样?”我对着空气低吼。没有回应。只有穿堂而过的冷风。母亲咳得更厉害了。
药不能停。钱像水一样流走。我再次找到孙瞎子,这次没绕弯子。“孙爷,您见多识广。
那‘琴魂’,到底是什么来历?有没有法子送,不是驱,是送走它?和和气气地送走。
”孙瞎子咂摸着旱烟杆,烟雾缭绕。“小子,你真问对人了。”他眯着眼,“早些年,
我听过一个说法。光绪年间,南边有个调琴的老匠人,姓胡,遇到过类似的事。
不是《广陵散》,是另一首古曲《离骚》。也是夜里弹,招了东西。”“他怎么解决的?
”“没解决。”孙瞎子吐出一口烟,“他死了。但他死前,留了句话给他徒弟。
说是‘曲有魂,因执念而生。知其所执,或可沟通,引其归去。’”“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得弄清楚,跟着你的这位,生前是谁,为什么独独放不下这首曲子,
为什么留在琴里。知道了它的执念,或许能跟它说上话,把它引去该去的地方。
”“怎么弄清楚?它又不说话,只跟着呼吸,还有……弹琴。
”孙瞎子敲敲烟杆:“它不是在跟你‘和鸣’吗?这就是它的‘话’。它弹的《广陵散》,
跟你的,有没有不同?调子?节奏?气韵?”3我愣住了。仔细回想,那夜它自己弹的片段,
生涩却精准。而跟我和鸣时,它的呼吸节奏……似乎在某些转折处,格外绵长或急促。
它在表达。用琴音,用呼吸。“还有,”孙瞎子压低声音,“这种老琴,
尤其是有‘东西’的,多半有来历。你试着查查‘孤桐’这个名字,或者琴身上的其他标记。
铺子里我是没听过,但有些老家族,或许有记载。”查?我一个落魄琴师,上哪儿去查?
母亲需要人照顾,我不能远行。我想到了一个人。宋修远。他是我师父的旧友,住在南城,
家里藏了些琴谱古籍,也爱钻研这些掌故。为人清高,不太与人往来。我上次见他,
还是师父去世时。我硬着头皮,买了些粗陋点心,登门拜访。宋修远见到我,有些意外。
听我吞吞吐吐说完来意,他眉头紧锁。“孤桐?”他沉吟着,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名字。”他引我到书房,翻找半天,
从一堆旧书里抽出一本没有封皮的册子,纸页脆黄。“这是我早年抄录的一些零散琴闻,
”他小心翻动,“你看这里。”我凑过去看。那是一段潦草的记述:“……崇祯末,
有琴师谢姓,名停云,世居金陵。琴技卓绝,性孤傲,尤以《广陵散》称绝。甲申国变,
痛彻心扉,携琴避祸南徙,途中遭匪,家小尽殁,唯余一琴。后隐于皖南山中,
常于月夜弹《广陵散》,声极悲怆,闻者断肠。忽一夜,曲未终而声绝。次日,
村人见其僵坐琴前,十指尽裂血染弦,目眦尽裂而亡。所用之琴,铭曰‘孤桐’。
琴遂不知所踪。后偶有传闻,谓谢停云魂附于琴,夜夜寻人共弹未竟之曲,
至死方休……”谢停云。明末的琴痴。国破家亡,孤身绝响。我盯着那几行字,手脚冰凉。
原来是他。怪不得执念如此之深。他死时,全部的心神、悲愤、不甘,
都凝在了那曲未终的《广陵散》里。他的魂,便困在了琴中,困在了每一个未尽的音符里。
他要的,或许不是害人。他只是想……把曲子弹完。“这是唯一的记载?”我问。
“就我见过的,是。”宋修远合上册子,面色凝重,“顾贤侄,若真是谢停云,
此事非同小可。他并非恶灵,而是至悲至痛之念所化。寻常法门,恐难‘驱散’。硬碰硬,
只怕激起更深的怨执。”“那该如何?”宋修远沉默良久,缓缓道:“或许,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完成它。”“完成?”“陪他,认认真真地,弹完一遍《广陵散》。
用你的全部心神,去理解他的悲愤,去应和他的琴音。不是敷衍,不是恐惧,
而是……真正的共鸣。让他觉得,找到了知音,曲终了,心愿或许也就了了。
”“若了不了呢?”我声音干涩。“若了不了,”宋修远看着我,“你可能就会像他一样,
成为这琴的一部分,永远弹下去。”我告辞离开,脚步虚浮。完成它?用我的命去赌,
赌一个三百年前枉死琴师的执念,能在曲终时消散?回到家,母亲已昏睡过去。
我坐在“孤桐”前,看着它。“谢停云,”我低声说,“你恨吗?”当然恨。恨匪祸?
恨天道?恨这夺走他一切的世道?我也有恨。恨贫穷,恨疾病,恨这看不到头的苦日子。
我们的恨,不一样。但又好像,有那么一点相通。都是被命运扼住喉咙,无法挣脱的人。
夜里,我没睡。我听着外间的动静。它没再自己弹琴。但我能感觉到,它在那里。它在等待。
或许,也在观察。4母亲没能熬过那个冬天。在一个极冷的早晨,她静静去了。
我握着她的手,直到它变得冰冷僵硬。世界彻底空了。我卖掉家里最后几件像样的东西,
草草办了丧事。债主又来了。这次,没了母亲的医药拖累,也彻底没了顾忌。“顾琴师,
这房子,你看……”我看着他们,指了指角落里的“孤桐”。“这琴,古物,抵债。
”他们找来懂行的。那人看了琴,验了又验,眼神发亮,又略带迟疑。“琴是好琴,
就是……阴气重了些。不过,总有识货又胆大的。这个数。”他比划了一下。足够还清债务,
还剩一点。债主拿了钱,走了。买琴的人来取琴那天,是个阴天。
我看着他们用锦缎将“孤桐”包裹,放入木匣。“谢停云,”我在心里说,
“你要跟着他们走了吗?”琴被抬出屋门。就在跨过门槛的刹那。啪!抬琴的伙计脚下一绊,
木匣脱手,重重摔在地上。锦缎散开,“孤桐”滚落出来,琴弦发出杂乱的嗡鸣。
伙计慌忙去捡。其中一个忽然“哎哟”一声,捂着手腕,脸色发白。“邪门!
刚才好像有人推我!”另一个伙计嘟囔着,小心翼翼把琴捡起,放回木匣。他们抬着琴,
匆匆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消失在巷口。心里没有轻松,反而沉甸甸的。
它真的走了吗?那一绊,是意外,还是……天黑下来。我收拾空荡的屋子,
准备明日搬去更便宜的住处。夜深了。我躺在那张冰冷的破床上,睁着眼。忽然。
我听到了呼吸声。极轻,极缓。就在我的床头。一下,一下。它没有走。它跟着我。
不是因为琴。是因为我。我弹了《广陵散》,我的“音”引来了它,
我的“恨”与它有了共鸣。它认准了我。我坐起身,对着黑暗。“谢停云,你到底要怎样?
”呼吸声依旧。但这一次,除了那冰冷的、如影随形的感觉,我似乎还感到了一点别的。
一丝……微弱的,几乎无法察觉的……焦灼?它也在着急?为什么?
因为我没能好好弹完那首曲子?因为我心里只有怕,没有懂?我闭上眼。回想宋修远的话。
“完成它。”赌一把。用我的命,赌一个解脱。我起身,走到外间空荡荡的屋子中央。
没有琴。我盘腿坐下,双手虚悬,仿佛面前有一张无形的琴。我闭上眼睛。在心里,
开始默奏《广陵散》。从第一个音开始。想象手指按上冰弦。想象旋律流淌。
我不再抗拒那份悲愤。我将母亲离世的痛,将自身潦倒的恨,将所有积压的绝望,
都注入这想象中的琴音里。我不是在模仿谢停云。我是在弹我自己的《广陵散》。
寂静的夜里,只有我越来越粗重的呼吸。但我“听”到了。那属于谢停云的呼吸,
就在我对面。一开始,它有些迟疑。然后,它渐渐跟了上来。与我的呼吸,
与我想象中的琴音节奏,慢慢合拍。我们之间,隔着一张不存在的琴。用呼吸,用心念,
共弹着一首千古绝响。我的“弹奏”越来越投入。那些指法、韵律,早已烂熟于心。
此刻在脑中流转,无比清晰。我感到一种奇异的交融。我的恨,与他的恨,
仿佛通过这无形的音,连接在了一起。我的眼前,不再是漆黑的屋子。
我“看”到了破碎的山河,流离的百姓,燃烧的宅院,还有……一个清瘦的背影,
在月下疯狂弹琴,直到吐血而亡。那巨大的悲痛,穿越三百年时光,重重撞在我心上。
我浑身颤抖,泪水涌出。不是恐惧。是共鸣。是同病相怜的悲怆。
我的“弹奏”进入了最激烈的“冲冠”、“长虹”段落。无形的杀伐之气在斗室里冲撞。
对面的呼吸也变得急促,剧烈,充满了积郁的爆发。我们一同,在这无声的琴曲中,
宣泄着所有的不平与愤怒。终于,曲近尾声。悲愤渐消,化为一片苍凉的余韵。最后一个音,
在我心中轻轻散去。我精疲力竭,虚脱般向前倒去,双手撑在地上,大口喘息,
汗水泪水混在一起,滴落尘土。对面的呼吸声,不知何时,变得极其微弱。然后,它停了。
那股一直萦绕在我周围的阴冷感,如潮水般退去。屋子里,只剩下我自己的心跳和喘息。
5月光从破窗棂照进来,清清冷冷。我抬起头。空无一物。它……好像真的走了。这一次,
是因为曲终了吗?因为有人,用全部的心神,陪他“弹”完了这一曲?我瘫坐在地上,
久久没有动弹。心里空落落的,却也好像,卸下了一块千斤巨石。我搬到了南城一处大杂院,
租了间最小的屋子。重新开始接些零散活计,用以前那张普通的琴。手指触弦时,
偶尔还会想起那冰凉的感觉,但很快散去。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轨。只是,
我再也弹不了《广陵散》。每次试图回想那旋律,心口就一阵揪紧,伴有莫名的虚脱感。
试过几次,便放弃了。也好,孙瞎子说过,不再碰那曲子,或许就安全了。几个月后,
我偶然在茶馆,听人说起一桩怪事。城东一个富户,新得了一张古琴,爱不释手。某夜兴起,
在书房弹奏。弹的什么曲子没人知道。但第二天,仆人发现他伏在琴上,已经没了气息。
十指指尖破损,面色青白,像是力竭而亡。那张琴,据说琴身乌黑,有蛇腹断纹。
名字就叫“孤桐”。听的人啧啧称奇,当个猎怪异闻。我却遍体生寒。它没有消散。
它回去了。回到琴里,继续等待下一个弹响《广陵散》的人。谢停云的执念,
并没有因为与我那一次无声的共鸣而消解。他只是……暂时满足了?离开了我的身边?或许,
他真正要的,不是一个知音。而是一个能让他“完整”重现死亡那一刻的……祭品。
那个富户,是在夜里弹琴而死。他弹的是《广陵散》吗?他死时,谢停云的魂,
是否就在他耳边呼吸,与他合奏,直到耗尽他最后一丝生命?我感到一阵后怕。如果那晚,
我面前有一张真实的“孤桐”,我是否也会像那个富户一样,在真实的琴音中力竭而亡?
我的那次“默弹”,究竟是送走了他,还是……仅仅让他暂时放过了我?没有答案。